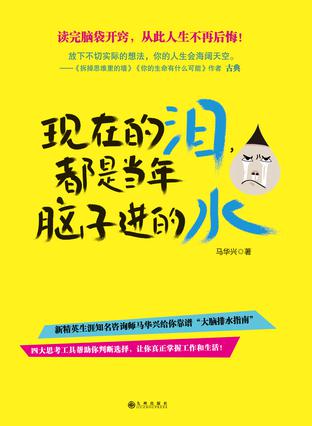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small>在我听说过的所有君主中,我能够想到惟一一个最接近真主精神的,就是巴格达的拉希德国王,这个人,你们都知道,很喜欢乔装成别人。</small>
<small>——伊莎·丹尼森</small><small>[1]</small><small>《七篇惊悚故事》</small>
<small>(选自《诺德奈的大洪水》)</small>
戴着墨镜走出《民族日报》大楼后,卡利普没有去他的办公室,而是走向“室内大”市场。他经过一家家卖游客纪念品的商店,穿越奥斯曼圣光清真寺的庭院,突然间,强烈的睡意袭来,伊斯坦布尔在他眼里突然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他看来,室内大市场里的手提皮包、海泡石烟斗、咖啡磨豆器都不像是属于这座人类定居了上千年的城市的物品。它们是可怕的符号,属于一个不可理解的国度,上百万的人民离乡背井暂居于此。“奇怪,”卡利普自忖,迷失在市场杂乱无序的骑楼里,“自从读出我脸上的文字之后,我可以乐观地相信,如今我能够彻底做自己。”
经过一排拖鞋店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相信,改变的不是这座城市,而是他自己。只不过,自从看出脸上的文字后,他就坚信自己已经解开了城市之谜,因此,他实在很难相信眼前的城市仍是他过去认识的那一个。望着一家地毯店的橱窗,他心中浮起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他曾经看过里头展示的地毯,曾经穿着沾满泥巴的鞋子和破烂的拖鞋踩在上面,仿佛自己跟坐在店门口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狐疑地盯着其他店的店老板很熟,似乎就像了解自己的一生那样,很清楚这家店的故事及其充满投机狡诈的历史、那弥漫着尘埃气味的过去。当他望着珠宝店、古董店和鞋店的展示柜时,也有同样的感触。匆匆扫视过几个骑楼店铺后,他开始想像自己知道室内大市场里卖的所有东西,从铜水壶到秤盘,而他也认识每一个等着顾客上门的店员,以及穿梭在骑楼里的每一个人。他实在太熟悉伊斯坦布尔了,这个城市在卡利普面前没有秘密。
他心情轻松,在骑楼里做梦似的闲逛。生平第一次,他眼前所见,不管是橱窗里的小摆饰还是迎面而来的脸,都既像梦中场景,同时又像嘈杂的家庭聚餐那样熟悉而令人安心。他经过一家珠宝店明亮闪耀的橱窗,心想,自己内心的平静必然与脸上的文字所指涉的秘密有关。虽然如此,他不愿意再去回想那具属于过去的可悲皮囊,那具自从他带着恐惧从脸上读出字母后,便抛在身后的残破躯壳。世界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里躲藏着第二个人,两个人就像双胞胎一样共同生活着。走过“补鞋匠市集”,那么懒洋洋的店员在门口打发时间,卡利普看见一家小店的入口处展示着鲜艳的伊斯坦布尔明信片,这时他才察觉,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双生兄弟留在身后了:这些明信片上全都是熟悉、陈旧、老套的伊斯坦布尔景象,那些老掉牙的风景名胜,像是停泊在加拉塔桥畔的公共客运渡船、托普卡珀皇宫的烟囱、黎安德塔、博斯普鲁斯桥。看着它们,卡利普更确定这个城市不可能有任何秘密瞒着他。不过,才一踏进贝德斯坦的窄巷,他的信心立刻消失。这里是旧市场的中心,酒瓶绿的商店窗户彼此对映。“有人在跟踪我。”他警觉地想。
附近没有半个人,但某种即将发生灾难的预感却叫卡利普顿时忧心忡忡,他加紧脚步快走。来到“毡帽师傅市集”时,他向右转,一路走到街尽头,然后离开市场。他本打算快步通过前面几家二手书店,可是当他经过“Alif书店”时,这些年来他从没多想过的店名却突然变成一个暗示似的。令人惊讶的,并不在于书店以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Allah”[2]为名——这不仅是真主“阿拉”这个字的首字母,而且根据胡儒非的说法,是字母和宇宙的起源——真正让人惊讶的,这个字,竟是如乌申绪所指示的那样,在门上方以拉丁字母拼成“Alif”。就在卡利普试图把它视为一个日常事件而非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时,他瞥见了穆阿马大师的店。这位扎玛尼教长的书店大门深锁——从前这家店的常客许多都是远方邻里的可怜寡妇,以及忧愁的美国亿万富翁——让卡利普认为,这仍然是隐藏在城市中的某个神秘符号,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比如说年长可敬的教长不想在寒冷刺骨的天气外出,或者是他死了。“倘若我还能在城市中看见符号,”他经过一堆又一堆老板放在店门口的翻译侦探小说和古兰经解析,“那么意思是,我还没有学会我脸上的字所教我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每次只要他想到自己被人跟踪,他的腿就会自动加速,使得整个城市从一个平静、充满了亲切的符号和物品的地方,转变成为一个可怕的场所,遍布着未知的危险和神秘。
走到巴耶塞特广场后,他转进“帐篷匠路”,然后踏上“俄国茶壶路”,只因为他喜欢这个路名。接着,他走上与之平行的“水烟袋路”,一路往下走到金角湾。接下来,他调过头,又沿着“铜钵路”走上坡。沿途经过塑料工作室、食品厨房、铜匠店和锁店。“这表示当我展开新生活时,早已注定会遇到这些店。”他天真地想着。再往前,他看到卖水桶、脸盆、珠子、金属饰片、军警制服的各种店家。他朝选定的目的地巴耶塞特塔的方向走了一会儿,然后调头,经过卡车、桔子摊、马车、旧冰箱、写着政治口号的大学外墙,一路走上伟人苏里曼苏丹清真寺。他走进清真寺的院子,沿着柏树前行,等脚上的鞋子沾满泥泞后,他从神学院旁的街道走出来,穿越一栋紧挨着一栋的原色木头房子。令他懊恼的是,他满脑子禁不住想着,从这些倾倒的屋子一楼窗口凸出来、伸向马路的排油烟管,看起来就“像”短猎枪,或“像”生锈的望远镜,或“像”吓人的加农炮管。然而他并不想把任何东西联想成别的东西,他也不想让“像”这个字眼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为了离开“青年热血路”,他转进“矮泉路”,一路上这个路名又盘踞了他的思绪,让他心想或许这又是个符号。老旧的石板路上充斥着符号的陷阱,他做出结论,决定走上“王子街”。在那儿,他观察到小贩沿街叫卖脆芝麻圈,小巴士司机喝着茶,大学生一边吃披萨一边研究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今天上演三部电影,两部是李小龙的功夫片,另一部,破损的海报和退色的照片中,康尼叶·亚金饰演一个塞尔柱的侯爵,打败了拜占庭的希腊人,与他们的女人睡觉。卡利普害怕自己若再一直盯着宣传照里演员橘黄色的脸,说不定会瞎掉,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过“王子清真寺”时,他努力把迸入脑中的“王子故事”甩开。他通过外围已锈蚀的红绿灯、一团混乱的涂鸦、头顶上方肮脏的餐厅和旅馆的广告招牌、流行歌手和洗洁精厂牌的海报。尽管他花费了很大力气一路上成功地把所有这些的隐藏意义全抛在脑后,但当他行经“瓦伦渠道[3]”时,他忍不住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里头的红胡子教士;当他走过著名的“微发”发酵饮料店时,他忍不住回忆起有一个假日夜晚梅里伯伯喝醉了酒,带着全家老少坐上出租车,来这里喝奶酒。这些画面当场便转化为符号,指向一个存在于过去的谜。
他几乎是跑着穿越阿塔图克大道,因为他再一次觉得,假使能走快一点,非常快,那么,城市呈现在他眼前的图画和文字就会如他想要的样子——它们真正的样貌,而不是一个谜的各种面向。他疾步走上“织布工路”,转进“木材市场路”,他走了好一会儿,不去留意任何街道的名称,沿路经过生锈的阳台栏杆与木头骨架交错而建的破烂连屋、1950年代长头型的卡车、被拿来当玩具的轮胎、歪斜的电线杆、遭拆除废弃的人行道、在垃圾筒间穿梭的野猫、站在窗口抽烟的包头巾女人、卖酸奶酪的流动摊贩、挖水沟的工人和制棉被的师傅。
才刚走下通往“祖国路”的“地毯商人路”没多久,他猛地左转,跨上另一侧的人行道,接下来他又这样变换了几次。来到一家杂货店,他停下来买了杯酸奶酪,一边喝一边想着,“被跟踪”的感觉必定是从如梦的侦探小说里得来的。他心知肚明,既然脑子里已摆脱不掉弥漫全城的无解之谜,更别想能把这股感觉抛之脑后。他转进“双鸽路”,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沿着“文化人路”几乎跑了起来。他闯红灯穿越“费维济帕夏街”,横冲直撞地闪过一辆辆小巴士。他瞥了一眼路标,赫然发现自己在“狮子穴街”上,剎那间他惊骇万分:如果,三天前在加拉塔桥上他察觉到的那只神秘之手,仍持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放置符号,那么,他确知存在着的那个谜,想必依然离他非常遥远。
他走进拥挤的市集,经过摊子上摆着青花鱼、八目鳗、比目鱼的鱼贩,来到所有道路的汇合点,亦即征服者清真寺的庭院。宽敞的院子里空无人迹,只有一个黑胡子男人,他穿身黑色外套,走起路来像是雪地里的乌鸦。小小的墓园里也没有半个人影。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的陵寝是锁上的,卡利普从窗子里望进去,聆听着城市的喧嚣:市集的嘈杂人声、汽车喇叭、远方一所学校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引擎发动的轰轰作响、庭院里树枝上麻雀与乌鸦的尖声鸣叫、小巴士和摩托车的怒吼、附近摔门和关窗的声响、建筑工地、房屋、马路、树、公园、海、船、邻近街区、整个城市的噪音。隔着雾蒙蒙的窗户玻璃,卡利普凝视着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那雕刻精美的石棺。这位他殷切渴望成为的人,五百年前征服了这座城市之后,就在胡儒非小册子的帮助下,开始凭直觉探索城市之谜。他一点一滴地对这片土地进行解析,在这里,每一扇门、每一座烟囱、每一条街、每一道沟渠、每一棵梧桐树都是符号,它们除了代表自身之外,都指涉着别的东西。
“要不是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让胡儒非著作和胡儒非信徒给牺牲了的话,”从“书法家路”走向“慈母智慧路”时,卡利普心里想,“要是苏丹能够揭开城市之谜的话,那么,当他走在他所征服的拜占庭街道上时,和此刻的我一样,看着颓圯的围墙、百年梧桐树、尘土飞扬的道路、空旷的空地,他可能会有什么心得呢?”等走到“节制区”的烟草工厂和恐怖老建筑时,卡利普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自从他读出脸上的文字后就明白的答案:“尽管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但他却熟悉得好像来过千万次了。”而惊人之处在于伊斯坦布尔仍只是一个刚被征服的城市。卡利普想不出究竟自己以前有没有见过、熟不熟悉眼前的景象:污湿的马路、碎裂的人行道、倒塌的围墙、可怜的铅灰色的树、摇摇晃晃的汽车和濒临解体的公交车、大同小异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狗。
现在他明白自己将甩不掉尾随在后的东西,即使他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总之他继续往前走,经过金角湾沿岸的厂房、空的工业用桶、拜占庭沟渠的断垣残壁、在泥泞的空地上吃面包夹肉丸当午餐或是踢足球的工人,直到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希望看到眼前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熟悉景象的宁静场所,使他禁不住想像自己是另一个人——是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他怀抱着这个幼稚的幻想走了好一阵子,也丝毫不觉得自己疯狂或荒谬。然后,他想到,许多年前耶拉曾在一篇纪念光复周年的专栏中说道,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到现今的一千六百五十年间,伊斯坦布尔曾经历过一百二十四位统治者,而其中,征服者穆罕默德是惟一的一个君王,不觉得自己需要在深夜里微服出巡的。“我们的读者很清楚原因何在。”当卡利普回想起耶拉文章里的这句话时,他正坐在斯克西—埃郁普的公交车上颠簸着。在温卡帕讷,他搭上了开往塔克西姆的公交车,他惊讶地发觉尾随的人竟可以那么快就跟上——他感觉那只眼睛更近了,就盯着他的脖子。到了塔克西姆又换了一次公交车后,他想,如果跟隔壁的老人说说话,或许自己可以转换成另一个身份,甩开背后的影子。
“你认为雪会继续下吗?”卡利普说,望出窗外。
“天晓得。”老人说,他似乎要再接下去说些什么,但被卡利普打断了。
“这场雪意味着什么?”卡利普说,“它在预告着什么?你知道伟大的鲁米有一则关于钥匙的故事吗?昨天晚上我梦见相同的东西。四周一片白,雪白,就像这场雪一样白。我突然惊醒,感觉到胸口一阵冰冷尖锐的疼痛。我以为有一颗雪球、冰球,或是一颗水晶球压在我心脏上,但并不是:躺在我胸口的是诗人鲁米的钻石钥匙。我伸手抓起它,爬下床,心想也许它可以打开我的卧室房门,果不其然。然而,开门之后我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床上正睡着一个长得像我但并不是我的人,他的胸口上也有一个钻石钥匙。我放下手里原本的那个钥匙,拿起第二个,打开门踏出这个房间,又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就这样我走进下一个房间,再下一个房间。无数个我的翻版,比我自己还要英俊,每人的胸口都放着一个钥匙。不单是这样,我看见房间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一群魅影般的梦游者,和我一样手里都拿着钥匙。每一间房里都有一张床,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像我这般做着梦的人!当下,我了解到自己身在天堂的市集里。那儿没有商业交易,没有金钱往来,没有税收缴纳,那里只有脸和形象。你喜欢什么,就去冒充什么;你可以像戴面具一样换上一张脸,从此展开新生活。我知道我所寻找的那张脸在最后一千零一个房间里,然而我手里拿到的最后一个钥匙却打不开最后一扇门。此时我才明白,惟一能开启最后一道门的,是我最初看到压在自己胸口的那个冰冷钥匙。可是,那把钥匙现在到哪去了?在谁手里?这一千零一个房间,究竟哪个才是我最初离开的房间和床铺,我完全没有头绪。我悔恨交加,眼泪直流,知道自己注定要和其他绝望的影子一起,跑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交换钥匙,惊异于每一张熟睡的脸,直到时间的尽头……”
“看,”老人说,“看!”
卡利普闭上嘴,隔着墨镜往老人所指的地点看过去。电台大楼前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具尸体,几个人围在旁边大呼小叫。很快地,集结了一群看热闹的民众,而交通整个堵塞了。公交车被卡得动弹不得,不管有座位或没座位的乘客,全部靠近窗边去看那具尸体,静默中透着恐惧。
等道路清空、公交车再度行驶之后,车内依然死一般的静。卡利普在皇宫戏院对面下车,到尼尚塔石一隅的安卡拉市场买了咸鱼、鱼子酱、切片牛舌、香蕉和苹果,然后疾步走向“城市之心”公寓。此时,他觉得自己太像别人,反而不想再当别人。他直接走向门房的家,以斯梅和佳美儿和小孙子们正在吃晚餐,围坐在铺着蓝油布的餐桌边,桌上是碎肉和马铃薯。这一幕和乐融融的家庭聚餐,在卡利普看来遥远得像好几个世纪前的场景。
“祝你们好胃口,”卡利普说,停顿了一会儿后又补充,“你们没有把信封交给耶拉吗?”
“我们按了好几次门铃,”门房太太说,“但他就是不在家。”
“他现在在楼上,”卡利普说,“所以,信封在哪儿呢?”
“耶拉在楼上?”以斯梅说,“如果你要上去找他,能不能顺便把他的电费单交给他?”他起身离开餐桌,走到电视机旁拿起上头的缴费单,一张一张凑到他的近视眼下查看。卡利普趁机摸出口袋里的钥匙,把它挂回架上的钉子。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动作。他拿了信封和电费单,然后转身离开。
“叫耶拉别担心,”佳美儿在他身后喊,兴高采烈的语气让人起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么多年来,卡利普今天第一次不讨厌搭乘“城市之心”公寓的老旧电梯,尽管电梯里仍飘散着亮光漆和机油的气味,上升的时候又像个腰痛的老头那样发出呻吟。镜子依然在原位,以前他和如梦常对着它互比身高,但此时他却不想看镜子,不想见到自己的脸,害怕自己会再次陷入文字带来的恐惧中。
他走进公寓,刚把脱下来的风衣和外套挂起来,电话就响了。拿起话筒之前,他先冲进浴室里为任何可能性做准备,凭着渴望、勇气和决心,他朝镜子看了几秒:不,那并不是偶然,字母、一切、整个宇宙和其奥秘都安然在位。“我知道,”拿起话筒时他心想,“我知道。”他知道电话的另一头必然是那个密报军事政变的人。
“你好。”
“这回你又叫什么名字?”卡利普说,“化名太多了,把我搞得头昏脑涨。”
“一个机智的开场,”对方说,声音里含着卡利普没有料想到的自信。“你替我取个名字吧,耶拉先生。”
“穆罕默德。”
“就好像征服者穆罕默德?”
“没错。”
“很好,我是穆罕默德。我在电话簿里找不到你的名字。给我你的住址,好让我去你那儿。”
“既然我把住址当成秘密,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心怀善意,想要把关于一场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的证据,提供给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太多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普通市民。”卡利普说。
“六年前我在凯尔斯火车站遇见一个家伙,”名叫穆罕默德的说,“一个普通的市民。他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而且就像八百年前的诗人阿塔尔那样,年复一年待在一家弥漫着药草和香水气味的普通小店里。他要到埃祖隆去处理生意。整段旅程中我们都在谈论你。对于你的家族姓氏——撒力克——的意义,他有一番见解:‘意思是苏菲之道上的旅人。’他很清楚你以真名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为何要用‘听’这个字来破题,原因是它翻译成波斯文是‘bishnov’,鲁米的《玛斯那维》正是以这个字开头。1956年7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把人生比拟为连载小说,而整整一年后,你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连载小说比拟为人生,这段时间,他对你的隐秘对称和功利主义深感兴趣,因为他从文字风格中分析出你以化名接下了摔跤手系列文章,这系列的原作者由于和报社之间有嫌隙而丢下不管。同时期的另一篇作品中,你要求男性读者不应该对街上的美丽女子皱眉,相反,应该要学欧洲人那样摆出爱慕的微笑。他知道你带着爱慕、景仰和温柔所描绘的美丽女子就是你的继母,你拿她来代表一个对男人的皱眉愤愤不平的女人。另一篇文章里,你暗讽一个住在伊斯坦布尔灰扑扑的公寓大楼里的大家庭,把他们比喻成一群可怜的日本金鱼住在鱼缸里。他晓得那群金鱼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叔叔养的,而那个大家庭便是你的家庭。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到过埃祖隆以西的任何地方,更别提来过伊斯坦布尔,但他却认识你所有不具名的亲戚、你居住的尼尚塔石公寓、附近的街道、转角的警察局、对面的阿拉丁商店、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中庭和院子里的倒影池、秋季花园、‘牛奶公司’布丁店、人行道沿路的菩提树和栗树。他对它们了如指掌,一如熟悉自己在凯尔斯市郊店铺里贩卖的各式南北杂货——从香水到鞋带,从烟草到针线。在那个年代,当我们的全国广播电台里还听不到统一的口音时,他知道你在‘伊斯坦布尔广播’里讽刺伊白亮牌牙膏所推出的‘十一个问题测验’,也知道他们为了奉承你好让你闭上嘴,拿你的名字用来作为价值两千里拉的答案。但正如他所料,你并没有接受这小小的贿赂,反而在下一篇专栏里建议读者不要使用美国制的牙膏,应该用他们自己干净的手,沾一点自制的薄荷香皂,来搓磨牙齿。你当然不会晓得,单纯善良的杂货店老板就依照你胡诌的配方,涂抹他那日后将会一颗颗脱落的牙齿。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火车旅程中,我和杂货店老板发明了一个问答游戏,叫做‘题目:专栏作家耶拉·撒力克’。我很辛苦地才赢了这个满心挂念要在埃祖隆站下车的男人。没错,他是个普通市民,一个提早衰老的人,一个没有钱修牙齿的人。这个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除了读你的专栏外,就是待在花园里逗弄他所养的好几笼鸟,然后跟别人谈论养鸟经。懂了吗,耶拉先生?一个普通市民也有能力了解你,所以你别想瞧不起他!不过,我碰巧比那位普通市民更了解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彻夜长谈。”
“第二篇提到牙膏的专栏后四个月,”卡利普开口,“我针对同一主题又写了一篇。内容在讲什么?”
“你提到,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在睡觉前给他们的父亲、叔伯、姑婶、继母们‘晚安吻’,漂亮的小嘴散发出薄荷牙膏的清香。平心而论,称不上是一篇专栏。”
“我还在其他什么地方谈到日本金鱼?”
“六年前,在一篇你向往着寂静与死亡的文章里。一个月后你再次带出金鱼,但这一次你说自己寻求的是秩序与和谐。你时常拿屋里的鱼缸和电视机相比。你给读者提供从大英百科全书里节录的新知,关于‘和金’金鱼因为混种而面临的大浩劫。谁替你翻译那些东西的?你妹妹还是你侄子?”
“那么,警察局呢?”
“它让你联想到深蓝色、黑暗、出生证明、小市民之悲、生锈的水管、黑鞋子、没有星星的夜晚、责备的脸、静止不动时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不幸、身为土耳其人、漏雨的屋顶,以及,自然而然的,死亡。”
“所有这些,你的那位杂货店老板,全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