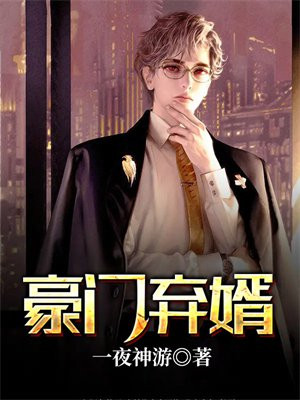26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
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small>十万个秘密即将揭示。当真相大白时,将出现惊讶的脸。</small>
<small>——阿塔尔《群鸟之会》</small>
晚餐时刻,尼尚塔石广场的交通逐渐舒缓,街角的警察也停止了愤怒的哨音,而卡利普已经盯着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整个人被掏空了,感觉不到眼前同胞的脸孔可能在他心里激起的悲伤苦痛。他的眼泪早已干了。精疲力竭的他,再也感觉不到那些脸可能带来的任何鼓舞、喜悦或兴奋,仿佛他对生命不再有任何期待。看着照片,他只感到漠然,像一个失去所有记忆、希望和未来的人那样;在他内心的一角感到一抹寂静,似乎将要逐渐蔓延,最终包裹住他整个身体。他甚至一边喝着浓茶、吃着从厨房里拿来的面包和羊奶酪,一边继续看照片,还把面包屑洒在上面。城市里雄心勃勃的喧嚣已平息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夜晚的声响。他可以听见冰箱的马达声、巷子底一家商店拉下木遮板的声音,以及阿拉丁商店周边传来的笑声。有时候他会注意到高跟鞋匆忙敲响人行道的断续节奏,有时候他则浑然不觉,尤其是当看到照片中的某张面孔,引起他一阵恐惧或是一阵耗神的惊异时。
于是他开始思考文字之谜与脸孔意义之间的关联,目的不是为了解开耶拉随手写在照片脸上的神秘暗语,而是有一股欲望,让他想模仿如梦那些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若要像侦探小说中的英雄那样,处处可以发现线索,”卡利普疲惫地想着,“惟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相信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他从走廊的柜子里拿出箱子,里头塞满了书本、论文、剪报、千万张照片和关于胡儒非教派的图像,再度展开工作。
他遇见几张脸,是由阿拉伯字母组成的,“眼睛”这个词当中包含wws和‘ayns,眉毛这个词当中包含zys和rs,“鼻子”这个词当中包含alifs。耶拉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字母一一标出来,像一个正在学习古字母的用功学生。在一本石版印刷书里的几页里,他看见好几只用wws和jms组成的泪眼,jms的那一点化成滑落纸页的一滴泪珠。在一张古老的黑白毛片中,他观察到同样的字母在眼睛、眉毛、嘴巴和鼻子里也清楚可辨。照片下方,耶拉以工整的字体写下拜塔胥大师的名字。在眼睛的形状和害怕的表情中,他看见“啊,爱的叹息!”的铭文、暴风雨中摇摆的战舰和天空劈下的闪电。他看见脸的轮廓中有各式各样的字母,如树枝般互相缠绕,每一撇胡子都画出不同的字母。他看见苍白的脸孔,眼睛从照片上被挖出两个洞;无辜的人,嘴角被写上文字,扭曲成罪恶的暗示;犯罪的人,前额的皱纹里刻上了他们可怕的命运。他注意到,许多被吊死的恶棍和总理脸上,浮着一抹心不在焉的神情,他们的眼睛望着脚踩不到的地面,一身白色囚袍,胸前挂着判决的罪名。他看到许多人寄来的各种照片:有的是知名影星的退色彩照,在她浓妆艳抹的眼睛里人们读出她其实是个妓女;有的是自认为有明星脸的人,寄来了神似多位苏丹、帕夏、鲁道夫·瓦伦蒂诺和墨索里尼的照片,并特地附上文字说明。从冗长的读者来信中,他发现一些端倪,透露出耶拉在玩的秘密文字游戏。有的读者解开了耶拉在一篇专栏中隐藏的信息,指出Allah(阿拉)最后一个字母“h”的特别含义和位置。有的读者花了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整年,分析出他用“早晨”、“脸”、“太阳”这些词所制造的对称。还有一些读者坚持认为耍弄文字游戏的罪过不下于偶像崇拜。他看见胡儒非教派创始者法兹拉勒的图片,翻印自古老的细密画,上头挤进了小小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他看见上头写着文字的足球运动员和电影明星图卡,那是阿拉丁商店卖的巧克力饼干和硬得像鞋跟的彩色泡泡糖盒里附赠的;他看见读者寄给耶拉的照片,里头有凶手、罪人和苏菲派大师。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市民同胞”照片,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过去三十年来从安纳托利亚各个角落寄给耶拉的一千张国人照片,有的来自破落的小镇,有的来自边远的村子,那儿的夏天艳阳晒得土地龟裂,而冬天里有四个月积雪冰封,除了饥饿的狼之外无人接近,有的来自叙利亚边界偷渡猖獗的村落,那儿的男人有半数因为误踩地雷而缺手断腿,有的来自四十年来痴等着公路开通的村庄,有的来自大城市里的酒吧和赌场,有的来自设置在洞穴里的屠宰场、烟毒贩的窝巢、偏僻火车站的站长办公室、牲口贩子赶集途中夜里住宿的旅舍大厅,还有一些则来自索乌克鲁克的红灯区。他看见几千张由街头摄影师的旧莱卡拍出来的照片,这些摄影师把相机固定在挂着邪眼[1]图案的避邪天珠的三脚架上,背景是政府办公室、市政大楼,以及代笔者替不识字的人打文件时用的折叠桌,接着他们就像炼金术士或算命师般消失在黑布下面,熟练地摆弄快门和折箱、黑色的镜头盖,以及用化学涂料处理过的玻璃盘。当这些市民同胞面对相机时,不难想像他们心里会升起一剎那模糊的死亡意识和永恒不朽的期盼。卡利普很快就明白,这股深沉的期盼,与他在脸孔和地图的符号中所察觉到的毁灭、死亡和挫败,密不可分。仿佛在巨大崩坏发生之前的多年幸福,已淹没在尘土下,火山爆发所喷出的灰烬早已将之掩埋,如今卡利普必须解读这成千上百个可疑的符号,才能从深埋的往事中找到失落的隐秘意义。
照片背后的资料透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寄到“观面相,知性情”专栏来的,这个专栏在1950年代初期由耶拉接手,那时他还负责谜语、影评和“信不信由你”。有些是应耶拉的征求而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读者的照片,并且在这些专栏中刊登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随着一些信件寄来,尽管信的内容卡利普读不大懂。他们面对镜头,表情好像想起某件陈年往事,或者好像注视着一道银绿的闪电击中地平线一片朦胧的土地,好像他们已习惯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运慢慢沉入一片黝黑的沼泽,好像他们是一群失忆症患者,深信他们永远唤不回自己的记忆。照片里,那些神情中的沉默,占据了卡利普的心。他很清晰地体会到为什么耶拉要在照片、剪报、脸孔、容貌上,刻下那些字句。可是,当他想利用这个理由来解开故事的结局时——关于他与耶拉和如梦相连相依的生命、关于离开这个幻影居所、关于他自己的未来——却顿时与照片中的脸孔一样陷入沉默。他的思想,原本应该要把各个事件编织出关联来,此时却完全被文字和面孔之间的意义迷雾所吞噬。就这样,他从脸上读到的那股恐惧慢慢逼近他,而他自己也一点一点地步入其中。
在拼字错误百出的石版印刷书和论文中,他读到了胡儒非教派的创立者兼先知法兹拉勒的生平。1339年,他出生于呼罗珊靠近里海一个叫做阿斯特拉巴德的城镇。十八岁时,他投入苏菲教派,展开朝圣之旅,随后在一位名叫哈珊教长的大师门下学习。为积累经验,法兹拉勒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间旅行,从亚塞拜然到伊朗,并且向大不里士、舍尔文和巴库的大师们请教。卡利普读到这里,心里油然升起想要“展开新生活”的急切渴望,就如这一类励志书里总会说的那样。法兹拉勒对于自己的命运和死亡,做了一些预言,日后果然成真,不过在卡利普看来,那些预测都只是平凡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准备新生活的人身上。最开始,使法兹拉勒为人所知的,是他会解梦。有一次,他梦见一对戴胜鸟、所罗门先知以及他自己。正当两只鸟站在枝头,看着所罗门和法兹拉勒在树下熟睡时,两个人的梦境融合为一,于是,枝头上的两只戴胜鸟也融合成为一只鸟。另一次,他梦见一位托钵僧来到他关闭的洞穴里拜访他,没多久,这位托钵僧果真来访,法兹拉勒才知道原来这位托钵僧也梦见了他。他们在洞穴里共同翻阅一本书,并在文字中看到了各自的脸,而当他们抬起头看见彼此时,却发现对方的脸上写着书中的文字。
根据法兹拉勒的观点,当每样东西从虚无跨入物质世界时,都会发出一个声响,因此声音是“存有”和“虚无”之间的界线:拿两个“最没有声音”的物品互相撞击,就足以让我们领悟这一点。而最进步的声音,当然了,便是“语言”,被称为“演说”的崇高之物,由字母拼凑而成的“文字”魔法。存在的起源,它的意义,以及真主创造的物质层面,都可以在人脸上清晰可见的字母之中找到答案。我们每个人都天生具备这些条件:两条眉毛、四排睫毛和一道发际线——总共七划。进入青春期后,逐渐成形的鼻子划分我们的脸,这个数字增加到十四。若我们再以稍为写意的方法勾勒笔画,加上想像和真实的线条,数字便增加一倍,显示出全部二十八个阿拉伯字母,证明穆罕默德用来创造古兰经的语言并非意外出现。若要把数字增加到三十二,等同于波斯字母的数目(法兹拉勒所说,和写作《永生之书》的语言),则必须更仔细地检视头发和下巴的线条,从中分成两半——各自又分成两条线,乘以二等于四。读到这里,卡利普才明白为什么箱子里照片中的人要把头发中分(模仿1930年代美国电影里的演员,把油亮光滑的头发从中分线)。这一切是如此明显,卡利普不禁为这种孩童般的简单明了感到欢欣鼓舞,觉得自己再一次理解了是什么吸引了耶拉投入这些文字游戏。
法兹拉勒宣称自己是信使,是先知,也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基督徒引颈期盼的再世基督、穆罕默德所预示的救主马赫迪——简言之,就是人们长年等待、耶拉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他”的那个人物。在七位信徒的拥护下,法兹拉勒开始在伊斯帕罕宣扬其信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法兹拉勒向人们传道,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充斥着许多隐而不察的秘密,若想要探究它们,必须先理解文字的奥秘。读到这里,卡利普的内心一阵释然,因为对他而言,这似乎清楚地证明了如今他的世界也充斥着秘密,一如他始终期待和渴望的那样。他内心的平静想必来自一个无比简单的推论:如果世界真的充满了秘密,那么,毫无疑问,桌子上的咖啡杯、烟灰缸、拆信刀,甚至他搁在拆信刀旁像一只犹疑的螃蟹的手,都指出一个隐晦的世界确实存在,它们本身也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梦在那个世界里,卡利普站在它的门口。不用多久,文字的秘密就会放他进去。
因此他必须更细心阅读。他又读了一遍法兹拉勒的生平,从中得知法兹拉勒曾梦见自己的死亡,后来也如做梦般地走向死亡。他被控散布异端邪说——崇拜文字、人类、偶像而非真主,宣称自己为救世主,并相信自己的幻想,追寻古兰经中所谓的隐晦之意,而不接受其真实明确的价值。他被逮捕,被拷问,最后处以吊刑。
法兹拉勒及其同伙被处决后,胡儒非信徒很难继续在伊朗待下去,于是他们长途跋涉进入了安纳托利亚,多亏了法兹拉勒的一位后继者,诗人内扎米的帮助。这位诗人把法兹拉勒所有关于胡儒非教派的书本和手稿,全装进一个绿色行李箱里——这箱子日后成了胡儒非信徒的传奇之物——然后游遍了安纳托利亚,访遍每一个小镇。为了寻找新的拥护者,他来到偏僻的神学院,那儿步调缓慢到在满室壁虎的检疫所和修道院里,就连蜘蛛都会忍不住打起瞌睡。为了向他的新学生解释,不只在古兰经里,其实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秘密,他诉诸文字游戏,灵感来自他很喜爱的棋戏。诗人内扎米能够在两行诗句中把他情人脸上的一个器官和一颗美人痣比喻为一个字母和一个句点,把这个字母和句点比喻为海底的一块海绵和一颗珍珠,把他自己比喻为一个愿意为珍珠而死的潜水员,把这位主动潜入死亡怀抱的潜水员比喻为一个寻找爱人的神祇,接着循环回到原点,把他的情人比喻为神。这样的一位诗人,后来在阿列坡被捕,经过一段冗长的拷问,最后遭剥皮而死:他的尸体被吊在城里公开示众,随后被切成七块,分别埋在七个城市里以儆效尤,那七个城市,正是他招纳信徒、人们朗诵其诗文的地方。
受到诗人内扎米的影响,胡儒非教派迅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拜塔胥人之间散播开来,甚至连十五年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也成了它的信徒。苏丹不仅随身携带法兹拉勒的著作,逢人便讲述世界的奥秘、文字之谜,以及他从新进驻的宫殿中所观察到的拜占庭秘密,甚至他会调查每一根烟囱、圆顶和树木,分别指出它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可以引领人探入另一个存在于地底下的谜样国度。当他身旁的神学家发现这件事后,便密谋迫害那些试图接近苏丹的胡儒非信徒,把他们活活烧死。
卡利普翻开一本小书,书的最后一页附了一张手写的纸条,说明(或误导)这本书是二次大战初期在埃祖隆附近的合罗珊暗中印制的。书中有几张图画,是胡儒非信徒在企图行刺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儿子巴耶塞特二世之后,被砍头或烧死的画面。另一页中,幼稚的笔触描绘出那些违反伟人苏里曼苏丹放逐令的胡儒非信徒,被火刑烧死时的场景和脸上骇惧的神情。火舌在躯体上跳跃,如同波浪,其中清晰可见“阿拉”这个字中的“alifs”和“lams”两个字母。然而更奇怪的是,在阿拉伯字母烈焰中熊熊燃烧的这些身体,它们眼睛里流下的泪水却被画成了拉丁字母的O、U和C。在此,卡普发现了胡儒非对1928年文字改革——从阿拉伯字母转为拉丁字母——的最早诠释。不过,由于他的心思是放在解开谜语的公式上,所以对此他没有多想,只是继续阅读从箱子里找到的东西。
他看到在书中许多地方都证实了真主的基本特质是一个“隐藏的宝藏”,一个谜。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去发掘它;在于我们要明了,这个谜其实反映在世界里;在于我们要理解,这个谜出现在任何事物、任何人之中。世界是一个充满线索的海洋,每一滴海水里所蕴含的盐分,都引向它背后的奥秘。卡利普红肿灼痛的眼睛越往下读,他心里就越清楚,自己终将洞悉海洋的秘密。
既然这些符号无所不在,那么奥秘也同样无所不在。就像卡利普不断在诗中读到的情人容颜、珍珠、玫瑰、高脚酒杯、夜莺、金发、深夜和火焰,他周遭的物品也是符号,不仅表示它们本身,同时也指涉着他正逐渐接近的神秘。被台灯的幽光照亮的窗帘、让他想起如梦的旧扶手椅、墙上的阴影、不祥的电话筒,这一切充满了故事和寓意,使得卡利普不禁感到自己正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到一个游戏中,就好像他小时候偶尔会有的感觉。但他继续往前,没有太多怀疑,因为他深信——和他小时候一样——只要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便能逃离这场吓人的游戏。“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把灯打开。”以前当他发现一起在黑暗中玩游戏的如梦也一样害怕时,他常这么对她说。“别开灯。”勇敢的如梦喜欢被吓,总是这么回答。卡利普继续往下读。
17世纪初,有些胡儒非信徒迁徙到一些边远的村落定居,当地的农民在亚拉立叛乱将安纳托利亚蹂躏成一片断垣残壁的时期,为了躲避各种帕夏、官员、盗匪和阿訇,早已弃村而逃。从一首长诗中可以读到,在这些胡儒非村落里,曾经一度弥漫着某种幸福充实的生活形态,卡利普一面想像这样的情景,同时不禁回想起自己与如梦共度的那段快乐童年。
在那段遥远的幸福岁月中,意义和行动始终是同义词。在那段黄金时期,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就是我们屋子里头拥有的东西。在那段过往的快乐年代,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手中的匕首和笔杆、工具和物品,都不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灵魂的延伸。那个时候,当一个诗人说到“树”时,每个人都能够正确无误地在脑中勾勒出它的样貌,每个人都知道,无须使用太多溢美之辞来列举它的枝叶,这个字眼和诗中的那棵树便足以解释“树”这个物品,也足以指涉花园里和生命中的一切。当时,每个人都非常明了,文字和它们所描述的事物是如此接近,以致当晨雾降临到山中这些幻影村落时,文字和它们所描述的事物已然融合。每当人们在云雾笼罩的清晨醒来,总分辨不出梦境与现实、诗歌和生活、名字和真正的人。那个时候,故事和生命是如此真实,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问哪一个才是最初的生命,或者哪一个才是最原始的故事。梦境在生命中上演,生命得到圆满的解释。和所有的东西一样,当时人们的脸也充满了意义,甚至那些不识字的人,尽管看不懂半个字母,却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读出我们脸上的文字,并参透其中的意义。
在那段遥远的快乐时光,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时间。诗人笔下的橘色太阳静静伫立在夜晚的天空中;船舰的大帆鼓胀着一股风,纹丝不动地在一片灰绿色的静止海洋上航行;洁白的清真寺和雪白的宣礼塔屹立在海边,像一座永不消失的海市蜃楼。卡利普读到这里才恍然明白,胡儒非的想像和生活尽管从17世纪以来始终隐藏而不为人知,其实却早已包围了伊斯坦布尔。诗文中描写的城里的景象:背后映衬着一座座三层楼的白色宣礼塔,鹳鸟、信天翁、骏鹰[2]和凤凰展翅高飞,迎向天际,几世纪以来它们就仿佛这样悬在半空中,从伊斯坦布尔的屋舍圆顶上方滑翔而过;在伊斯坦布尔那些总是歪斜交汇、毫无章法的街道上,每一个出游的人都好像是踏上一段永恒的假日之旅,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夏日的温暖月夜里,从井里不仅能汲取冰凉的水,也能够捞起满满一桶神秘的符号和星光,那时人们会彻夜吟诵诗歌,诉说各种符号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多样表征。看到这里,卡利普才明白,伊斯坦布尔曾经存在过一段纯粹美好的胡儒非教派年代,这让他更清楚,自己与如梦共度的快乐时光已然远去。
这段幸福的时代想必为时不久。卡利普读到,黄金年代结束后,很快地这个神秘信仰就变成了众人鄙夷的污点,而关于它的秘密也变得更复杂难解。为了更进一步隐藏他们的秘密,有些人会求助于神符圣水,他们学居住在幻影村落里的胡儒非信徒们,用鲜血、蛋、头发、粪便,调制出各种混合物;其他人则在伊斯坦布尔的隐蔽角落和自己家的地底下挖掘隧道,以埋藏他们的秘密。然而有些人则没有挖隧道的人那么幸运,他们因为加入禁卫军叛乱而被逮捕,吊死在树上,上过润滑油的绳索像领带一样缠绕脖子,勒得他们的脸部文字扭曲变形。不仅如此,当吟游诗人拿着鲁特琴,来到陋巷里的托钵僧小屋低声传唱胡儒非的奥秘时,结果也只是碰壁,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卡利普所读到的这些证据,证实了曾经存在于偏远村落也存在于伊斯坦布尔小街暗巷的黄金年代,在一夕之间消失。
卡利普手中的这本诗集,书页有老鼠咬啮的痕迹,角落长出一朵朵深绿和蓝绿色的霉菌,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纸张和潮湿的气味。翻到最后一页,他看到一则批注写着,关于这个主题在另一篇专论中有更详尽的资料。在诗的最后一行下面与印刷厂地址、出版社、著作和出版日期的上面,留了一点空间,合罗珊的排字工人塞进了密密的一行又长又不合文法的句子,指出同系列中的第七本书由同一单位在埃祖隆附近的合罗珊出版,作者是乌申绪,书名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曾获得伊斯坦布尔记者歇林·卡马兹的高度评价。
昏昏沉沉的卡利普,满脑子都是关于如梦的梦境和充满文字的幻想,疲惫又失眠,此时不禁联想到耶拉刚进新闻业的最初几年。那个时候,耶拉所玩的文字游戏,只限于在“今日星座”和“信不信由你”专栏中,用暗语传递讯息给他的情人、家人和朋友。为了找出批注中提及的专论,他在几大叠文件、杂志和报纸中胡乱翻找,满屋子翻箱倒柜。最后,他终于在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箱子里找到了那本书,埋在一堆耶拉收集的1960年代初期剪报、未发表的辩论和一些怪异照片中。这时早已过了半夜十二点,街道上笼罩着肃杀的静寂,像是戒严国家的宵禁气氛,叫人背脊发凉。
如同许多这一类的“著作”,往往过早宣布出版时间,而真正的发行日总拖了很久,《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也隔了好几年,一直到1967年才终于在另一个城镇果德斯问世——卡利普很惊讶当时那里竟然有印刷厂——装订成一本两百二十二页的书。泛黄的书封上是一幅图画,印刷很糟,想必是出自粗糙的制版和廉价的油墨:那是一幅简陋的透视法插画,一条左右栽种了两排栗子树的道路,往前延伸通向看不见的远方。每一棵树的旁边都印着文字,恐怖、让人浑身冰凉的文字。
乍看之下,它很像几年前某些“理想主义”的军官所写的书,内容关于“为什么过去两百年来我们赶不上西方国家?我们该如何进步?”这些由作者自费在某个安纳托利亚偏僻小镇印刷的书,最前面常有类似的献词:“军事学校的同学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不过,把书翻开之后,卡利普便明白在他面前的是一本截然不同的“著作”。他从椅子上起身,来到耶拉的书桌前,把两只手搁在书的两侧,开始专心阅读。
《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前两部的标题正好是书名。第一部,“文字之谜”(或者可说是胡儒非之谜),从胡儒非教派的创始者法兹拉勒的生平开始说起。作者乌申绪在故事中加入了较为入世的层面,不纯粹把法兹拉勒描述为一个苏菲派和神秘主义学者,更视他为理性主义者、哲学家、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如同人们认为法兹拉勒是个先知、救世主、殉道者和圣人——或者还不只这样——他也是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和天才,虽然“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他的思想解释为泛神论,或是像西方国家某些东方主义学者那样,用普罗提诺、毕达哥拉斯、卡巴拉的观点来分析法兹拉勒,这些方法,都会像是用法兹拉勒一辈子抵抗的西方思想来捅他一刀。法兹拉勒是一个纯粹的东方人。
依照乌申绪的说法,东方与西方分别占据半个世界:两者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彼此矛盾——如同善与恶、黑与白、天使与恶魔。与活在梦幻中的乐观主义者的假想相反,乌申绪认为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完全不可能和平共处。两者之一必然会控制另一个,一个扮演主人的角色,另一个则是奴隶。为了描绘这对孪生兄弟之间不曾止息的争斗,作者回顾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并且一一列举:亚历山大割断戈耳迪之结[3](作者评注说:“意思正是解谜”)、十字军东征、拉希德国王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神奇时钟上头各种文字和数字的双重意义、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伊斯兰在安达卢西亚的胜利(作者花了整整一页探讨科尔多瓦清真寺的石柱数目)、本身是胡儒非信徒的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征服拜占庭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哈扎尔人的崩毁、最后是奥斯曼人先后在多皮欧(《白色城堡》)和威尼斯的围城挫败。
乌申绪认为,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指向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而法兹拉勒则把它转化为各种隐喻,融入他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之所以能够压制对手的原因,绝非偶然,而是确有逻辑可循。任何一方,若能成功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看出这个世界是一个模棱两可、充塞着秘密的神秘地方,那么,这一方就会占上风,得以支配另一方。相反,把世界视为单纯、清晰、有条有理的那一方,则注定会失败,结果必然是受到奴役。
乌申绪在书本的第二部里,详尽地讨论了谜的失落。所谓的谜,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指古希腊哲学家的“理念”、新柏拉图学派基督教的“神性”、印度教的“涅槃”、阿塔尔的“骏鹰”、鲁米的“挚爱”、胡儒非的“秘密珍宝”、康德的“本体”,或者是一本侦探小说中的凶手。不管谜究竟是什么,任何时候,它都意味着“中心”,始终隐秘不为人知。如此一来,乌申绪解释,若一个文化失去了“谜”的概念,便丧失了它的“中心”,一个人如果观察到此现象,必然要推论出这个文化的思想也已经失去了平衡。
接下来的几行,卡利普读得似懂非懂:鲁米必须要谋杀他的“挚爱”,也就是大不里士的贤姆士;为了保护他所“设置”的谜,他展开大马士革之旅;然而,在城市里的漫游和搜寻并不足以支持这个“谜”的概念;鲁米为了要重新定位自己已经偏离的思想“中心”,在流浪途中去了许多场所。作者认为,一场完美的谋杀案,或是一个不留痕迹的失踪案,都是重新建立失落之谜的好方法。
随后,乌申绪着手铺陈胡儒非教派中最重要的课题,“文字与脸”之间的关系。仿效法兹拉勒在著作《永生之书》中的做法,他说明在人类的脸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见总是隐而不为人知的真主,他详尽地检视了人脸上的线条,把这些线条勾画成阿拉伯字母。作者花了许多篇幅,天真地分析胡儒非诗人的诗句,比如说内扎米、雷费、米撒里、巴格达的鲁赫伊和罗丝·巴巴,最后整理出某种逻辑。当处于幸福昌盛的年代时,我们所有人的脸孔都富有意义,就如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这个意义要归功于胡儒非信徒,因为他们看出了世界的谜和世人脸上的文字。然而,随着胡儒非教派的消失,我们脸上的文字以及世界的谜,也一起失去了踪影。从此以后,我们的脸孔变成空白一片,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从中读出什么,我们的眉毛、眼睛、鼻子、目光和表情只剩下空洞,我们的脸不再具有意义。虽然卡利普很想起身照镜子看看自己,但他继续仔细往下读。
摄影艺术带来了悚然黑暗的结果,由于直接以人为题材,它展现出我们脸上的空虚,就好像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电影明星脸上特殊的五官起伏,会让人联想到看不见的月亮背面。而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和开罗的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仿佛深夜里躁动呻吟的鬼魂;所有男人皱眉的脸上全都蓄着相同的胡子;所有戴着同款式头巾的女人全都流露出相同的目光。这一切都随着空虚而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统,来分辨那些将会在我们空白的脸上重新灌输意义的拉丁文字母。书的第二部最末,作者愉快地告诉我们,整套系统的运作即将在题为“谜之发现”的第三部中公之于世。
乌申绪不仅善用言外之意,而且喜欢玩弄文字,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使得卡利普不禁对他产生好感。他的某个方面,让人联想起耶拉。
[1]地中海地区的迷信,若诸事不顺,可能是有嫉妒你的人对你下了邪眼诅咒。此区文化当中因而常以邪眼图案作为护身符。
[2]骏鹰(Simurgh),古波斯传说中的巨鸟,为狮与鹏鸟的结合体。
[3]戈耳迪之结,希腊神话中,佛里几亚王戈耳迪的难解绳结,根据神谕所示,能解开这个结的人,便能成为亚细亚王,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以剑将它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