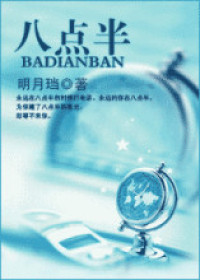阿摩司·奥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尤里将汽车停在本·迈蒙大道上,这时已是五点一刻了。太阳已经落到松树和柏树的后面去了,但还有一片浅灰色的奇异的光亮逗留在空中,光亮中充满了朦朦胧胧、忽隐忽现地闪烁的东西,那是一种既非白天又非晚上的光亮。本·迈蒙大道和所有的石头建筑上空弥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啮噬人心的安息日前夕的忧郁。似乎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又变成了一场噩梦。
雨停了。空气湿润湿润的,费玛的鼻孔捕捉到一股烂树叶的强烈气味。他想起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现在这样的时间,在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他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骑自行车。朝这幢大楼一看,他看到父亲和母亲都站在阳台上。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同样高的个子,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靠得很近,但没有挨着。就好像是一对蜡像。在费玛的印象中,他们是在哀悼一个迟迟不来、都已经让他们苦等得绝望了但他们还是要期待下去的客人。当时,他平生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他整个童年时期,父母之间那连绵的沉默中隐藏着深深的羞耻。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分歧。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沉默。他下了自行车,腼腆地问是否到他进屋的时间了。
巴鲁赫说:
“随便。”
母亲什么也没说。
这段回忆唤醒了费玛心中一种迫切的需求,他要澄清什么,他要问问尤里,他要打听打听。他觉得自己忘了核实那件最最要紧的事情。可最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他可就不得而知了。虽然他觉得自己此时无知的程度要比平常浅些了,就像后面能见到模糊影子在活动的蕾丝窗帘。或者就像一件只供蔽体但再也无法保暖的破烂衣服。同时,他在骨子里知道,他是多么渴望继续无知下去啊。
他们爬楼梯上三楼的时候,费玛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尤里的肩膀上。尤里似乎很疲惫,很忧伤。费玛觉得有必要通过碰触的方式来鼓舞一下他这位大块头朋友。这位大块头朋友一度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是现在,他走到哪里也都将脑袋咄咄逼人地向前突出着,腕上戴着一只精密的航空表,那一双眼睛有时让人觉得,他无论看什么都是从上到下地俯视。
可他仍是一个热情、诚实、衷心的朋友。
大门上固定着一块长方形黄铜门牌,门牌上是几个灰底黑字:农贝格宅第。门牌下面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卡片,巴鲁赫在卡片上遒劲有力地写道:下午一至五点,请勿按铃。费玛下意识地瞥了一下自己腕上的手表。不过也没有必要按铃了,因为门是半敞着的。
茨维·克鲁泡特金在大厅里截住了他们,就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参谋,受命向新来的人介绍情况,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进入作战指挥室。尽管救护车司机罢工,他说,安息日又即将来临,不知疲倦的尼娜还是通过她办公室的电话做了妥当的安排,让他的遗体转到了哈达萨医院的太平间。费玛觉得又一次喜欢上了茨维那种腼腆的窘态:他看上去不像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和系主任,倒更像一个外来的、双肩已经开始下垂的青年活动领导人,或者是一个乡村教师。费玛也喜欢茨维那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的样子,似乎光亮突然强烈起来了似的;喜欢他心不在焉地触摸凡是他手指能够碰到的东西的习惯,碟子啦,家具啦,书啦,人啦,似乎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在私下里怀疑是否坚固,似乎他总要跟自己秘密的怀疑搏斗。如果不是出于对耶路撒冷的狂热,如果不是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对犹太人责任的执着,这个谦逊的学者说不定已经在剑桥或是牛津定居下来了,然后就平平安安地活到一百年,把他的时间分割在高尔夫球场和十字军东征上面,或者分割在网球和丁尼生[1]的诗歌上面。
费玛说:
“你们将他转移走了是对的。让他整个周末都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在客厅里,朋友们将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向他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肩膀、他的脸颊、他的头发,似乎通过他父亲的死,他继承了病号的角色。好像他们有义务要认真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感到太热,还是感到太冷,还是在发抖,还是在心里打算着不辞而别。舒拉将一杯蜂蜜柠檬茶塞到他手上。特迪则轻轻地将他按坐在散落着刺绣坐垫的织锦面沙发的一端。大家似乎都在期待地等着他说些什么。费玛说:
“你们都太好了。我很抱歉就这样把你们安息日前夕的时间都给搅和了。”
父亲的扶手椅立在那里,恰好面对着他:深深的,宽宽的,红皮面子,还有一个红皮头靠,整个看上去就像是用生肉做成的。脚凳似乎已被人轻轻地推到了一边。那根像君主权杖的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靠在扶手椅的右侧。
舒拉说: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遭受一点儿痛苦。一会儿就结束了。是以前人们通常所谓的‘一吻而终’:只有义人才被赐予这样的死法,过去的人们通常都这样说。”
费玛微笑着说道:
“义人也好,不是义人也好,反正接吻一直是他全部本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说着的时候,他注意到一种他以前从没注意到的情况:舒拉,这个三十多年前他与之约会的女人,在公羊年前他与之约会的女人,当时还有着一种脆弱的少女般的美丽,如今已经衰老了,头上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白发。事实上,她的两条大腿已变得那么肥胖,以致看上去就像一个由于生儿育女而被弄得疲惫不堪但却彻底放弃抵抗地接受了老朽状态的极度虔诚的女人。
在房间里放置了多年、摞成一厚堆一厚堆的地毯以及古董家具发出一股浓烈逼人的气息,久久地萦绕在房间里,费玛于是不得不提醒自己:这气息一直就在这里,并不是克鲁泡特金教授夫人衰老的气息。与此同时,他的鼻孔捕捉到了一丝烟味。朝四周一看,他看见一只烟灰缸的边沿上放着一支香烟:几乎一点着就给掐灭了。他问是谁一直在这儿抽烟的。原来是他父亲的两位女友,那两位前来募捐的老妇人当中的一位,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马上就将其掐灭了。是她注意到巴鲁赫在大喘气才将香烟掐灭的吗?还是当一切都已结束了的时候?还是就在他呻吟着断气的当儿?费玛要求将烟灰缸挪走。看到特迪立即跳将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他不觉高兴起来。茨维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抚弄着中央暖气管道,问他愿不愿意上那儿去。费玛不明白这个问题。简直无法控制尴尬情绪的茨维对他解释说:
“上那儿。到哈达萨医院。去看他。说不定……”
费玛耸了耸肩。
“上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想他还会同平时一样地衣着整齐。干吗要打扰他呢?”他嘱咐舒拉给尤里冲一杯浓郁的清咖啡,因为他上午一下飞机就在忙个不停。“事实上,你还应该给他做点儿东西吃才是:他这会儿肯定饿坏了。我估摸着他必定是凌晨三点的样子就离开了他在罗马所住的那家酒店,所以他实际上过了漫长又辛苦的一天。不过真的,你自己看上去也很疲惫,舒拉;事实上,你看上去像是精疲力竭了。约珥和迪米这会儿在哪里?我想让约珥到这儿来。还有迪米。”
“他们俩在家里。”特德抱歉地说,“小男孩简直接受不了。可以这么说,他对你父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接下去又说,迪米将自己独自锁在杂物间里,他们于是不得不给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朋友打电话,向他讨教该怎么办。心理学家告诉他们,随他去好了。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迪米就出来了,接着就黏在了电脑上。南非的朋友建议他们……
费玛说:
“混蛋。”
接着,语气平静地,但是坚定地,他说:
“我要他们俩都到这儿来。”
说这话时,他为在父亲去世后他重新获得的这种果决感到惊奇。好像父亲的去世让他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次提拔,让他从此以后就能随便地发号施令,并且让自己的命令一刻也不耽搁地得到服从。
特德说:
“当然。我们是可以把他们俩叫来。可是根据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最好还是……”
费玛趁这个请求还没有出口就将其扼杀了。
“你最好还是别介意。”
特德犹豫了一下,又和茨维叨咕着商量了一番,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好吧,费玛,不管你想要什么都成。好的。我立马回去,把迪米带过来。如果尤里不介意把钥匙借给我使用一下的话,约珥把我们两人的车子拿去用了。”
“请把约珥也带来。”
“好的。我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呢?看看她是不是能来?”
“她当然能来的。告诉她,我坚持要她来。”
特德出去了,这时尼娜又到了。她身材矮小瘦削,办事讲究实际效果,动作像剃刀般麻利,狐狸一样的瘦脸上透露出对世事的通达和生存适者的机敏,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似乎她这一天不是在安排葬礼,而是在烈火中抢救了一天的伤亡人员。她穿着一条浅灰色的裤套装,眼镜片在那里闪着光亮,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只硬邦邦的黑色公文包,就在她飞快地侧拥了一下费玛并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将公文包放下来。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舒拉说:
“我打算到厨房里给你们每人都弄点儿喝的。有谁要喝的?喝点儿什么?有没有人要煎蛋饼呢?要么是面包片夹点什么?”
茨维吞吞吐吐地说:
“还有,他是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是那样充满活力。他眼睛那么一眨巴可有意思了。他对生活、对美食、对生意、对女人、对政治等等都是那样热爱。前不久他还到我在斯科普斯山的办公室去了,对我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耶沙亚胡·莱博维茨是在蛊惑人心,通过迈蒙尼德捞取资本。我试图表示异议为莱博维茨辩护的时候,他又哇啦哇啦地讲开了一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德洛霍维茨[2]、在梦里见过迈蒙尼德的拉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挚爱。我以前总以为他会活到高龄的。”
好像是在对一起并非由他引起的争执发布最后裁决似的,费玛宣告说:
“事实上,他已经活到高龄了。准确地说,他毕竟不是英年早逝。”
尼娜说:
“我们将所有的安排都办理妥当了,这可纯粹是奇迹。一切都安排在星期天了。相信我好了,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可真是一场同时钟的疯狂赛跑。[3]我们的耶路撒冷现在比德黑兰还要恶劣。我们没有等你,你不生气吧,费玛?你等于消失不见了,我这才擅自做主,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免得你头痛。我已经安排在《国土报》和《晚报》上刊登讣告了。也许我还应该安排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了。葬礼的安排我们也做好了,是后天,星期天,下午三点。原来,他已经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地皮,但不是在桑海德里亚,即你母亲旁边的墓地,而是在橄榄山。顺便说一句,他还为你买了一块临近的地皮。就在他旁边。关于葬礼,他还在遗嘱里作了详细、周到的交代。他甚至还选定了赞礼员,是他的一个犹太同乡。也纯粹是一个奇迹,我还是设法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就在安息日到来前的一分半钟在电话里将他逮住了。他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墓志铭上的措词。是一篇韵文什么的。不过墓志铭的事可以等到第一个月结束,如果不是等到周年结束的话。如果因他乐善好施而得益的人有四分之一来参加葬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至少五十万人的估计。包括市长、各色拉比和政客在内,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肝肠寸断的寡妇和离婚妇女了。”
费玛一直等她说完了,这才轻声地问道:
“你自己把遗嘱打开了?”
“在办公室里。当着几个证人的面。我们只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