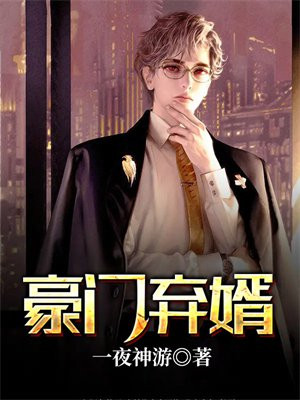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small>一般而言,大家都是以貌取人。</small>
<small>——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small>
星期二早晨,当卡利普坐回被报纸专栏淹没的书桌前时,他的心情不像前一天早上那样乐观。经过第一天的工作后,耶拉在他心里的形象已经改变,使得调查似乎失去了焦点。但是别无他法,他只能继续阅读从走廊柜子里取出的专栏和笔记,抽丝剥茧出耶拉和如梦的藏身处,因此当他坐下来阅读时,不禁有一种孤注一掷面对灾难的满足感。除此之外,待在一个充满快乐的童年回忆的房间里阅读耶拉的作品,远胜过坐在斯克西脏乱的办公室里,审阅为了保护房客对抗严苛房东所拟的契约,以及钢铁和地毯商彼此针锋相对的文件。虽说这由一场不幸引起,但他感觉到一股干劲,像是一个公务员被派往更好的位置处理更有兴趣的工作。
他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兴致勃勃地把手边的线索复习了一遍。他想起塞进门缝的《民族日报》里标题为“道歉和反讽”的专栏,几年前已经刊登过了,说明耶拉星期天没有交出新文章。这是该专栏第六次使用旧稿——档案夹中只剩下一到两篇备用稿。这意味着,假使耶拉不赶快生出一篇新作,那么他的专栏马上要开天窗了。过去二十五年的每一天,卡利普都以耶拉的专栏为生活揭开序幕,而耶拉无论生病或休假,也从不曾拖欠过任何一篇文章。因此,每当卡利普想到第二版上出现空白专栏的可能性时,总会感到浩劫即将来临的忧惧。这样的浩劫,让他联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
为了确保不错过任何可能自动送上门的线索,他把抵达公寓当晚拔掉的电话线再度接上。他回想自己与自称马海尔·伊金西的男人在电话中的对话,那人提到的“卡车谋杀案”和军事政变让卡利普想起耶拉过去几则专栏。他从盒子里拿出那些文章,仔细阅读之后又想到耶拉一些关于救世主的文句和段落。他花了好长时间,凭着印象和日期找出这些分散在各式各样文章中的段落,最后再次坐回书桌前时,他已经累得仿佛工作了一整天。
1960年代初期,耶拉试图利用他的专栏煽动军事政变,那时他一定记得自己在谈论鲁米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原则:一个专栏作家,若要让一大群读者接受某个概念,必须有办法重新修复读者记忆库里熟睡的回忆,再次搅动那逐渐腐朽而沉淀的思想残渣——像是黑海深处一艘艘沉船里的尸体。身为忠实的读者,卡利普期待通过阅读耶拉依此宗旨而写作的故事,搅动他记忆库里的沉渣,只不过,被激起的是他的想像力。
读着《武器的历史》中所提到的第十二个阿訇,在室内大市场里那些偷改秤盘刻度的银楼老板之间引起恐慌;被自己父亲宣称为救世主的教长,带领着库尔德族牧羊人和铁匠师傅,从堡垒发动攻击;一个洗碗工助手,梦中看见穆罕默德驾着一辆白色敞篷凯迪拉克驶过贝尤鲁的污泥石板路,从此之后他便声称自己为救世主,煽动妓女、吉普赛人、扒手、香烟小贩、擦鞋童和游民,起来反抗地头蛇和皮条客。卡利普眼前浮现这些场景,笼罩在砖红和橘黄的氤氲中,如同他自己的生命与梦境。还有一些故事,不仅开启他的想像力,也触动了他的记忆:关于猎人阿合迈的事迹,这个冒牌货,在自封为王储进而自立为王后,更自称为先知。读到这里,卡利普想起耶拉有天晚上——如梦在旁边微笑着,一如往常透过乐观而惺忪的睡眼望着他——思索着一个问题,若要设计一个“冒牌耶拉”,能够代替他写专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一个能够探入我记忆库里的人。”他这么说,听来奇怪。)卡利普猛地一阵惊恐,感觉自己正被拖进一场危险的游戏,等着他的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他再度检查耶拉的通讯簿,拿上头的姓名电话去对照市区电话簿。他找出两边不符合的,试打了几个电话:第一个打到拉雷利的一家塑料公司,他们制造洗碗盆、水桶、洗衣篮,只要提供模型给他们铸模,一星期内便能生产并运送出上千个各种颜色的任何物品。第二个电话是一个小孩接的,他告诉卡利普,他和妈妈、爸爸、奶奶一起住在这里。不,爸爸不在家。在话筒传到焦虑的妈妈手上之前,一个之前没提到的哥哥插话进来说,他们不会把名字告诉陌生人。“你是谁?你是谁?”紧慎而恐惧的妈妈说。“打错了。”
等卡利普看完耶拉在公车票和电影票根上的信手涂鸦后,已经是中午了。其中一些纸片上,耶拉艰难地写下他的观影心得,另一些上面则记下演员的名字。有的名字下面画了底线,卡利普猜不透原因何在。几张公车票上也写着姓名和文字:其中一张(十五库鲁的车票,显示它是1960年代发行的)上面,有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凑组成的脸。就这样,他阅读着票上的文字、影评、一些早年的专访(知名美国影星玛莉·马罗昨天来访!)、填字游戏的草稿、他随手捡选的读者来信,还有几张新闻剪报,内容是耶拉计划写的几件贝尤鲁凶杀案。大部分案件都大同小异:全都使用厨房的尖刀,全都发生在半夜;犯罪的原因除了当事人喝醉酒外,更是由于好勇斗狠的本性。报道中的强硬口吻反映出这样的道德观:“混黑道的人下场就是如此!”耶拉把报纸上的一些数据,拿来用在“伊斯坦布尔观光景点”(奇哈格、塔克西姆、拉雷利、古图路斯)专栏的几篇文章里,重新叙述凶杀案的故事。卡利普看到一系列“历史上的第一次”连载,想起土耳其第一本用拉丁字母编写的书籍,是在1928年,由教育图书社的发行人卡辛姆先生出版。这个人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知识性日历附时刻表》,一大本厚如砖头,让人每天撕下一页。每一页上面都印着——除了如梦最爱的每日菜单外,还有阿塔图克的格言,或是杰出的伊斯兰人物,或外国名人,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波特佛里欧,以及轻松小语——一个钟面,指示当天各节祷告的时间。其中几张没撕掉的日历上头,耶拉在钟面上乱动了手脚,把指针画成圆脸上的尖鼻子或长胡须。这使得卡利普相信自己发现了一条新线索,赶紧拿出一张白纸记下来。吃午餐的时候(面包、奶酪、苹果),一股莫名的兴致让他开始翻笔记。
一本笔记本里,记载着两本翻译侦探小说的摘要(《金甲虫》和《第七封信》),以及一些密码和暗语,选自几本有关德国间谍和马其诺防线的书籍。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他看见一道颤抖的绿色钢珠笔笔迹。线条看起来有点像开罗、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地图上的绿色墨水痕迹,又似乎有点像人脸,或是像花,也颇像曲折的溪流,蜿蜒滑过一片平原。卡利普跟随着不对称而无意义的曲线从第一页走到第四页,接着在第五页的地方解开了笔迹之谜。答案是有人把一只蚂蚁放在一张空白页的中央,然后拿一支绿色钢珠笔紧跟着焦急逃命的昆虫,在它身后留下凌乱的轨迹。来到第五页后,精疲力竭的蚂蚁绕着圈子,画出犹豫不决的轨迹,最后在纸张的中央,留下一具被人压扁的干尸。不知道这只倒霉的蚂蚁因为无力提供任何解答而被人处决,是多久以前的事?而这个奇怪的实验与鲁米的文章又是否有所关联?卡利普展开调查。在《玛斯那维》的第四部中,鲁米曾提到有一只蚂蚁爬过他的草稿:一开始,蚂蚁注意到阿拉伯字母中藏着水仙和百合花的影子,接着有一支笔创造出这片文字花园,接着有一只手引领这支笔,再接下来有一个智慧生物控制着这只手。“而最后,”耶拉在他的文章中补充,“它察觉到还有另一个至高的智慧,带领着这个智慧生物。”卡利普本想对照笔记和专栏的日期,从中建立一个合理的联结,但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只记录了伊斯坦布尔历史性大火的地点、日期以及所烧毁的木造房舍数目。
他读到耶拉的一篇文章,内容讲到在20世纪初期,有一个二手书商的学徒,趁挨家挨户推销的时候暗中耍阴谋。这位书商学徒每天搭小船往来城市各区,前往有钱人家的宅邸,把行囊里的特价书卖给后宫女眷、深居的隐士、工作繁重的职员和爱做梦的孩子。不过,他真正的顾客则是各地区的帕夏。由于阿布杜哈米提苏丹的限制令,这些官员被软禁在公府和自家宅院里,受到苏丹情报单位的监控。书商学徒向帕夏们(耶拉称之为“他的读者”)泄露胡儒非的秘密,以便教导他们如何解读他黏在这些书本里的文章。读到这里,卡利普感觉自己逐渐转变为另一个人,而这正是他想要的。这些秘密,他后来才发现,只不过是一本精简版的美国小说末尾出现的符号和关键词。当他们小的时候,某个星期六中午,耶拉曾经拿这本以远洋为背景的小说给如梦看。明白这点之后,卡利普确信自己绝对能够通过阅读,变成另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刻,电话响了,打来的人,当然了,就是上次那个家伙。
“很高兴你把电话线接回去了,耶拉先生!”他说,声音听起来像是过了中年的人。“眼前有这么可怕的情况迫在眉睫,我压根儿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与城市和国家脱节。”
“你查到电话簿的第几页了?”
“我很认真在找,但比预期的要花时间。查电话号码查太久,会让人胡思乱想起来。我在里面看到了魔法配方、几何对称、重复排列、矩阵变化以及数字的各种形状,这拖慢了我的速度。”
“也有脸吗?”
“是的,不过你的那些脸孔是由某些数字的排列组合而来的。数字不见得都会说话,有时它们沉默无语。有时候我依稀感到4想要告诉我什么,一长串的4,一个接着一个。一开始先是两个两个一组,接着它们不见了,整排换到下一列去,现在变成了16。然后,7取代了它们空出的位置,依循同样井然有序的音调低声呢喃。我想说服自己一切只是巧合,没有意义,可是你看,帖木儿·巴耶塞特的电话号码140-22-40,难道不会让你联想到1402年帖木儿大帝和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之间的安卡拉战役?以及接下来,野蛮的帖木儿赢得胜利后,抓走了巴耶塞特的妻子,纳入自己后宫?电话簿活生生地展现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历史!我不禁沉迷其中,忘了找你的地址这件事。但我知道你是惟一能够阻止这场大阴谋的人。他们蓄势待发,箭在弦上,而你就是那根紧绷的弓弦,耶拉先生,惟有你阻止得了这场军事政变!”
“怎么说?”
“上次在电话中,我并没有告诉你,他们误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救世主身上,徒劳地等待着他的降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士兵,读过几篇你早年写的文章,并且深信不疑,就像我一样。试着回想一下你自己在1961年时写的几篇专栏,回忆一下你谈论‘审判长’的赞诗,以及你的一些影评,还有你那篇高傲文章中的结论,你在里面畅谈为什么你不相信全国乐透彩券上的幸福家庭肖像(妈妈打毛线,爸爸看报纸——或许是读你的专栏——儿子念书,奶奶和猫咪坐在炉火旁打瞌睡:假如每个人都这么该死的幸福美满,假如大家都像我的家庭一样,那么为什么乐透彩券会卖得这么好?)。当时,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批评家庭伦理剧?这些影片为数不清的人带来无数的乐趣,或多或少替大家表达了心声,但你所看到的,却是其中的布景、梳妆台上的古龙水瓶、久未弹奏而结满蛛网的钢琴上成排的照片、塞在镜框周围的明信片,以及家庭收音机上熟睡的小狗雕像。为什么?”
“我不知道。”
“哈,不对,你知道!你指出这些物品,是为了呈现我们的悲惨和颓败。同样的道理,你提到被扔进通风井中的破烂物品、住在同一栋公寓楼的大家族、近水楼台而结婚的堂兄妹,以及铺在扶手椅上防尘防脏的布套。在你的笔下,这些物品成为令人痛心的符号,代表着我们的自甘堕落和无可避免的腐朽。但不久之后,你又自圆其说,在你所谓的历史评论中暗示,永远有获得解放的可能:在最黑暗的时刻,将会出现一位救主,带领我们脱离贫瘠的生活。这位或许好几世纪以前就曾来过此地的救主,将会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复活:继五百年前以耶拉列丁·鲁米或谢伊·加里波的身份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后,这一次,他将以某位报纸专栏作家的身份复出!虽然你只是把这一切放进你的文章中,娓娓道出贫民窟里等待汲取公共泉水的女人的悲哀,呐喊着铭刻在旧街车木头椅背上的爱情誓言,然而,这些军人却把你的话当真。他们以为,当他们所信仰的救世主来临时,一切的悲苦和哀愁都将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光明与正义。是你鼓动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你写作的对象!”
“那么,现在你想要我怎么样?”
“只要见到你就够了。”
“何必?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机密文件,对不对?”
“如果能够见你一面,我会向你解释清楚。”
“你的名字显然也是捏造的!”卡利普说。
“我想见你。”那个声音说,听起来像一个配音员用矫揉造作、却又诚挚感人的声音说“我爱你”,“我想见你。等你见到我之后,你便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见你。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没有人。我知道你彻夜做梦,一边喝着自己泡的茶和咖啡,一边抽着你放在暖炉上烤干的马帝皮香烟。我知道你的文章是用打字的,并用一支绿色钢珠笔修改。我知道你不满意你自己,也不满意你的生活。我知道许多夜晚,你郁郁寡欢地在房里踱步,直到黎明破晓。你渴望成为另一个人,而不要做自己,但你始终无法决定该选择哪一个身份。”
“这些全是我写的!”
“我也知道你不爱你的父亲,当他带着新太太从非洲回来后,他把你赶出你长久居住的阁楼公寓。我也知道当你搬进你母亲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时光。啊,我的兄弟!当你还是个穷酸记者时,你专跑贝尤鲁线,编造了各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案。你在佩拉宫饭店所采访的美国电影明星,不仅根本不存在,连电影也是假的。为了写一篇土耳其鸦片烟瘾者的自白,你干脆自己吸食鸦片!你以假名替人代笔一篇摔跤手的连载故事,结果到安纳托利亚采访的时候,被人痛打了一顿!你在‘信不信由你’专栏中,写下了字字血泪的自传故事,但读者根本感觉不到!我知道你有手汗的毛病,你出过两次车祸,你一直找不到防水鞋可以穿,你害怕孤独但又老是独来独往。你喜欢攀登宣礼塔,在阿拉丁商店里闲逛,和你的继妹谈天说笑,也喜欢色情书刊。除了我,谁还会知道这些事情?”
“很多人,”卡利普说,“谁都可以从文章里读出这些。你到底说不说你为何非得见我不可?”
“因为军事政变啊!”
“我要挂电话了……”
“我发誓!”声音听起来焦虑而绝望,“只要让我见到你,我就会告诉你一切。”
卡利普把电话线扯下来。他从走廊柜子里拿出一本毕业纪念册,昨天第一眼瞥见这本书后,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坐进耶拉每晚精疲力竭回家后瘫坐的椅子,卡利普翻开这本装订精美的1947年军事学校毕业纪念册:最前面是阿塔图克、总统、参谋总长、三军统帅、总司令和军事学校教职员的照片及箴言,后面则印满了全体学生一张张整齐的照片。页与页之间都夹着一张葱皮纸作保护。卡利普一页页翻,也不懂为什么在讲完电话后会突然想看这本纪念册。他只觉得上面的面孔和表情惊人地雷同,就好像头上的帽子和领子上的军阶条饰一样。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在看一本老旧的古币收藏手册——与一堆廉价旧书一起塞进好几只脏纸箱,堆在二手书店门口展示——银币上所刻的人头和文字只有专家才鉴别得出差异。他意识到心中升起了一股旋律,那是当他走在路上或坐在候船室时所察觉的那一缕乐音:他喜欢观察脸。
翻动着书页,他回想起,以前他常等好几个星期,终于拿到最新出版的漫画书,当他急匆匆翻开散发着油墨和新纸气味的书页时,心中的雀跃之情难以言表。的确,与漫画书的内容一样,每件事都连接到另一件事。他开始在照片中看见他之前在路人脸上发现的剎那光彩:似乎照片也能够像真人面孔一般,向他展现丰富的意义。
1960年代初期那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中,绝大多数的筹划者——除了那些向年轻军官眨眼示意、自己却撇清关系的将军们之外——想必都是出自这本纪念册的年轻军官。书页上,或是表层的葱皮纸上,散布着耶拉的涂鸦,但都跟军事政变毫无关系,倒有点类似小孩子替照片中的脸加胡子,或是在颧骨和鼻子下方涂一抹淡淡的阴影。有些额头上的纹路,被修改成“命运纹”,依稀可辨几个无意义的拉丁字母;有些人的眼袋被加重画成O或C的图样;还有一些人的脸饰以星星、牛角和眼镜。几位年轻军校生的下颚骨、额骨和鼻梁骨都被标上记号,画上比例尺线,有的线条纵贯脸盘,有的线条横贯鼻子、嘴唇和额头。有些照片下方作了标记,对应其他页的照片。军校学生的脸上被加上各式各样的青春痘、痣、雀斑、阿列坡疣、胎记和伤疤。其中有一张脸特别明亮无瑕,让人无从加上任何线条或字母,在这张照片的旁边,有一行字:“修改照片将抹杀其灵魂。”
卡利普在另外几本纪念册中也看到相同的句子。他发现耶拉在各种纪念册大头照上都留下了类似的线条和记号:工程学院全体学生、医学院教职员、1950年国会议员、席瓦斯—开塞利铁路兴建工程人员、“布尔萨美化协会”组员,以及伊兹密尔市阿尔珊查克区的朝鲜战争自愿军人。几乎每一张脸都用一条直线垂直平分成两半,以便凸显左右两边的文字。卡利普时而草草翻阅,时而花工夫仔细检视照片:仿佛他想抓住灵光乍现的片刻,努力挽回眨眼间即被永远遗忘的某段记忆;仿佛他正摸索着路径,试图重返某个深夜一度误闯的房舍。有些脸光瞥一眼就能彻底看透,但有些平静的面容却出乎意料地隐藏着故事。不知不觉地,卡利普想起好几年前一部外国电影里一位短暂出现的服务员眼神中的色彩和忧愁,以及最后一次在收音机里听见的一首曲子,一段他期盼着,但总是错过的旋律。
夜色逐渐降临,卡利普从走廊的柜子里拿出所有的纪念册、相册、照片剪报,以及从各处搜集来在盒子里堆积如山的照片,把它们全部拿进书房,像个酒鬼似的一张张浏览。他分辨不出有些脸是在何时、何地又为何被拍下来:照片里有年轻女孩、头戴瓜皮帽的绅士、包着头巾的女人、表情诚恳的男子和贫困潦倒的穷人。不过,有些悲伤的脸被拍摄的地点和原因倒是再明显不过:两位市民在一群阁员和安全警察的和蔼注视下,焦虑地望着他们的国会议员代表向总理陈递请愿书;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和铺盖,侥幸逃离贝希克塔斯区贝瑞布佑街的火灾现场;一群女人在阿尔罕布拉戏院前面排队买票,为了看埃及演员阿布杜·瓦哈伯主演的电影;一位著名的肚皮舞娘和一位电影明星因为持有大麻被捕,在警察的陪同下出现在贝尤鲁市区车站;一个会计师,因为侵吞公款而被逮捕时,脸上刷地呈现一片空白。这些照片,似乎自己解释了它们存在和被保留的原因:“还有什么,能比一张照片,一个人脸部表情的写真,更为深奥、迷人、令人好奇的呢?”卡利普想。
他悲伤地想到,即使在最“空洞”的脸背后,在那些经过修片和其他摄影技巧的调整而失去意义和表现力的照片里,也隐藏着充满回忆、恐惧和秘密的故事,无法用言语传达,只能从眉眼中的哀愁看出来。卡利普热泪盈眶地看着这些照片:一个制棉被学徒中了全国乐透头彩时,快乐而恍惚的脸;一个保险业务员,在持刀砍杀妻子后的表情;前往欧洲大陆“以最佳仪态代表土耳其”的土耳其小姐,在欧洲小姐选美比赛中荣获亚军时的神情。
他暗自思忖,贯穿耶拉作品中的那一丝忧郁,必定源于目睹这些照片。有篇文章提到一座能俯瞰工厂仓库的出租公寓,院子里晾了一排衣物,这想必受我们的业余拳击冠军在出战五十七公斤量级比赛时脸上的表情的启发;有篇文章探讨加拉塔歪斜的街道只有在外国人眼中才显得歪斜的理论,这想必是由于看到了一名自称曾和阿塔图克上过床的一百一十岁女歌手青白的面孔。而一群从麦加朝圣回来途中遇上车祸的信徒,他们戴着小圆帽的尸体上的脸,让卡利普联想到一篇关于伊斯坦布尔旧地图和版画的文章。在那篇专栏中,耶拉写道,某些地图上的符号,标记着宝藏的位置,同样地,某些欧洲版画中的符号,则向意图前往伊斯坦布尔行刺苏丹的狂热杀手,透露秘密讯息。卡利普心想,耶拉窝在伊斯坦布尔某个藏身处好几星期写出的那篇文章,一定与他用绿笔做记号的那些地图有某种关联。
他念着伊斯坦布尔地图上的地名,诵读它们的音节。但是这些字眼多年来每天被重复百遍,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联想,以至于对卡利普而言,它们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就好像“这样”、“那样”之类的词。相对地,那些在他生命中印象模糊的地名,当大声复述时,便立刻令他产生联想。卡利普想起耶拉曾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伊斯坦布尔某些地区的景象。于是他翻出从柜子里拿来的“伊斯坦布尔的幽僻角落”系列,开始阅读。然而他发现,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在描述伊斯坦布尔的偏僻地区,还不如说是一篇篇短篇小说。若是在别的时候,自己被这样摆了一道,他可能一笑而过,但此时的他却感到无比地灰心,因为显然耶拉一辈子都在故意欺骗他的读者,甚至包括卡利普。他一边读这些街坊轶事——从法蒂赫开往哈比耶的电车上爆发的小口角,费里克伊一个小孩在走出家门去商店跑腿后就失踪,或是钟表店里那一只有音乐滴答声的钟——同时不停地默念:“我不会再信以为真了。”然而没多久,他又忍不住猜想耶拉或许就窝在哈比耶、费里克伊或托普哈内的某处。这使得他原本对耶拉的满腔怒火,转到自己身上,气自己的心理偏执,老是想从耶拉的文章中找线索。他厌恶自己总是在追求情节故事,就好像那种随时随地都想要玩的小孩一样。他立刻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空间可以容纳符号、线索、第二层和第三层意义、秘密和谜语,所有的符号全是他内心为了企图解开疑惑而幻想出来的产物。他多么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个单纯的世界里,一切物品只是物品本身。惟有那样,这些字母、文章、脸孔、街灯、耶拉的书桌、梅里伯伯从前的柜子、留着如梦指纹的剪刀或钢珠笔,才不再是透露弦外之音的可疑符号。在那儿,绿色钢珠笔就只是绿色钢珠笔;在那儿,谁都不渴望成为另一个人。究竟人如何才能进入那样的世界?卡利普研读着桌上的地图,像个孩子幻想自己居住在电影里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希望能说服自己,他就生活在那另一个世界中:剎那间,他仿佛看见一个老人满是皱纹的额头;接着,他眼前出现历代苏丹脸孔的合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朋友的脸——或者,那是一个王子?——但他还来不及细看,脸孔就又消失了。
几分钟后,他来到安乐椅前,坐了下来,打算翻看耶拉三十年来搜集的大头照,他心想这些影像必然来自他渴望前往的另一个世界。他随手抽出照片,尽量不去注意脸上的符号或秘密。于是,每张脸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物,组合了眼睛、鼻子和嘴巴,跟身份证和户籍文件上的照片没什么两样。其中,他瞥见一张黏在保险文件上的女子照片,那秀丽而意味深长的面容中隐含的忧郁,带给他一阵哀伤。接着,他振作起来,看另一张没有丝毫哀愁和故事的脸。为了不想和脸上的故事有任何牵连,他甚至避而不读照片下方的文字,或耶拉在旁边写下的说明。就这样好长一段时间,他逼着自己像欣赏人脸地图一样,浏览这些照片。等尼尚塔石的夜晚又再度车水马龙,而眼泪开始溢出眼眶时,卡利普才看完了一小部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