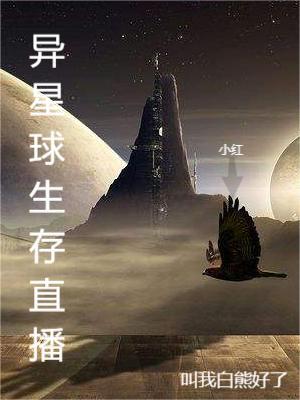阿摩司·奥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谁许可你这么做的?”
“非常坦白地说……”
“在哪儿呢?我是说遗嘱。”
“在这儿,在我公文包里。”
“给我。”
“马上?”
费玛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那只黑色公文包。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棕色信封。他默默地走了出去,独自站在阳台上。一千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父母就站在阳台上,看上去就像一对遭遇船舶失事而身陷孤岛的幸存者一样,此刻他就站在他们当年恰好站立的地方。最后一缕光亮早已暗淡下来了。本·迈蒙大道上的寂静飘拂上来。街灯闪烁着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其间飘流着一片片云雾。所有的石头大楼都无声地立在那里,每家每户的百叶窗都关闭着。大楼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偶尔刮过一阵风,传来十字架谷[4]的狗吠声。第三种状态是一种恩赐,只有放弃一切欲望,只有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时间、没有比赛、没有任何东西地站在夜空下,才能达到。
可有谁能够这样站立在夜空下的呢?
在他童年时代,就在这儿的雷哈夫亚居住着一些个头矮小、举止优雅的学者,就好像瓷人似的,一个个都是迷惑不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街上举起帽子彼此打招呼。好像要在脑海里抹掉希特勒似的。就好像要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从不存在的德国似的。因为他们宁愿让人觉得心不在焉或是荒唐可笑也不愿让人觉得傲慢无礼,所以甚至在他们还无法肯定正朝他们走来的人到底是不是朋友或熟人的情况下也会把帽子举起来,只是看上去像是朋友或熟人时也把帽子举起来。
费玛九岁的时候,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他和爸爸正在阿尔法西街散步。巴鲁赫停下脚步,和一个穿一套老式西装、打一条黑色蝶形领结、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人用德语(也可能是捷克语)没完没了地聊开了。最后,小孩子的耐心给耗尽了,他一边跺脚,一边在那里拉扯着爸爸的胳膊。父亲朝他脑袋就是一巴掌,用俄语冲他吼叫着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鼻涕虫!”后来,他对费玛解释说,那人是个教授,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他对他解释“世界闻名”是什么含义,如何才能“世界闻名”。费玛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番解释。这个词语至今还让他既感到敬畏又觉得鄙夷。又有一次,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是一天早晨的六点半,他和父亲在拉什巴姆街上散步,他们忽然看见本·古里安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短步走过来,本·古里安当时就住在本·迈蒙大道和乌色什金大街的拐角,喜欢每天凌晨轻快地散上一会儿步,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巴鲁赫·农贝格抬起帽子说:
“先生,能否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呢?”
本·古里安停下脚步惊呼道:
“是卢帕廷!你在耶路撒冷干什么?谁在守卫加利利?”
巴鲁赫平静地答道:
“我不是卢帕廷,而你,先生,也不是弥赛亚。你那些近乎瞎眼的追随者肯定在你耳朵旁边小声叨咕着什么,但我建议你不要听信他们的话。”
总理说:
“什么,你不是格里沙·卢帕廷?你肯定没有弄错吗?你看上去太像他了。这么说,这回是弄错对象了。如此说来,你是谁呢?”
巴鲁赫说:
“我碰巧是属于敌对阵营的。”
“相对卢帕廷来说吗?”
“不,先生,相对你来说。还有,如果我能够冒昧地说一句……”
但本·古里安已经开始向前迈开步子了,他只是一边走一边说:
“好吧,敌对,敌对。可不要过于忙着敌对,以致没能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抚养成以色列的忠实爱国者、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土地的捍卫者。其他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事。”这样说着,他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后面跟着一个其作用显然是防止他受到骚扰的英俊的男性保镖。
巴鲁赫说:
“成吉思汗!”
然后又补充道:
“埃弗雷姆,你自己想想上帝选择谁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了:是约坦所说‘树的寓言[5]’里的荆棘。”
当时,十六岁的费玛每当想起他吃惊地发现本·古里安原来个头比他自己还要矮,大腹便便的,生着一张大红脸和一双侏儒短腿,嗓音就像骂街泼妇的那样又粗又大,他就暗自好笑。父亲要对总理说些什么呢?现在,经过思考之后,他自己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那个忽略了加利利守卫任务的卢帕廷或者卢帕特金到底是谁呢?
约珥不想保留的那个孩子长大后难道就没可能世界闻名吗?
还有,迪米怎么样?
突然,费玛来了一阵灵感:他明白,从事喷气式汽车研究工作的约珥事实上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可能取得巴鲁赫一直为他所梦寐以求的荣誉。他问自己,他到底是不是约坦所说“树的寓言”中的荆棘呢?茨维卡,尤里,特迪,尼娜,约珥——他们都是会结果的树,只有你,约韦勒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先生,一辈子都是在制造愚蠢和谬误。对着别人喋喋不休尽说些无聊话,骚扰大家。同蟑螂和蜥蜴争论。
他为何不做出决定,从今天就开始,或者是从明天就开始,把自己余下的日子都用来为他们铺路呢?他要肩负抚养迪米的重担。他要学习做饭和洗涮。每天早晨,他要把画图板上的所有彩色铅笔都削好。他要经常为电脑更换色带。如果电脑有色带的话。因此,和那个他并不知晓的士兵一样,他要谦卑地为喷气式汽车的开发和约珥摘取“世界闻名”的桂冠做出自己的些微贡献。
在他的童年时代,在雷哈夫亚这儿,每到暖烘烘的夏夜就能听到一架钢琴透过紧闭的百叶窗发出寂寥的声音。甚至连沉闷的空气也似乎在模仿那些声音。而如今,那些声音都去了,被人忘记了。本·古里安和卢帕廷已经死了。那些戴着无边圆帽、打着领结的难民学者也死了。在他们和约泽尔之间,我们这些人撒谎、通奸、屠杀。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松林和寂静。还有书脊烫金字已经开始褪色的某些破烂的德语巨著。
突然间,费玛不得不忍住自己由于渴望而想流的泪水。并不是对那些死者的渴望,也不是对曾经在这儿存在过、如今又不复存在的东西的渴望,而是对那些本当有可能存在但事实上又没有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的一切的渴望。他脑海里突然想起“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他不管怎么费力去想,就是想不起来他是听谁在最近两三天里说出了这句恐怖的话。
现在,他突然觉得这句话是那么精当,那么鞭辟入里。
耶路撒冷周围山顶上的光塔,将阴森森的修道院团团包围起来的、上面是锋利碎玻璃的废墟和石墙,沉重的铁门,生铁做的格栅,地窖,阴暗的地下室,一个沉思、愤恨的耶路撒冷,深陷于那些被石头砸死的先知、被十字架钉死的救主以及被斧头劈成碎块的救赎者的噩梦里,被一带草木不生、岩石密布的山峦团团围住,被山洞和沟壑弄得凹凸不平的斜坡的那种空旷,差不多不再是树木而已经加入了无生命王国的背信的橄榄树,跌宕起伏的开裂山谷中那些寂寥的矮小的石头房子,远方向南延伸到曼德海峡、向西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向北延伸到哈马和巴尔米拉的一片片浩瀚的沙漠,毒蛇横行的土地,由白垩和盐组成的广袤的土地,领着一群群黑山羊、外袍褶皱里塞着复仇利刃的游牧牧民时常出没的所在,沙漠中的黑帐篷,环绕在所有这些之中的是雷哈夫亚和它在黄昏时分从那些小房子里传出的忧郁的钢琴声,它那些羸弱的老学者,它那些层层书架上摆放着的德语巨著,它那种彬彬有礼,向上高高举起的无边圆帽,下午一至五点的寂静,水晶枝形吊灯,流放的上漆家具,织锦和皮革做成的扶手椅面子,成套的细瓷餐具,餐具柜,父亲那种容易激动的俄罗斯人脾性,还有本·古里安和卢帕廷,那些忧郁学者书桌旁苦行僧般的光轮,他们正在积累别人引用他们文献时所做的脚注,正通向“世界闻名”之路,而我们呢,我们无助地、无望地、迷惘地循着他们的足迹,茨维卡研究哥伦布和天主教会,特德和约珥研究他们的喷气式汽车,尼娜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安排清算,瓦尔哈夫提格在他那个堕胎的地狱奋力捍卫一块文明的地盘,尤里·格芬漫游世界,征服女人,用他那冷嘲热讽式的幽默来调侃自己的征服经历,安妮特和塔马,没人需要,你自己则研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和蜥蜴争论,在深更半夜给伊扎克·拉宾写信,探讨在道德衰败时期暴力的代价。还有,迪米在想着他那只被惨杀了的狗。所有这些都将何去何从呢?前往雅利安人那边的琳又是在什么地方迷路了呢?
似乎这儿并不是一座城市的一个分区,而是那些在世界尽头定居的捕鲸者的一块遥远营地,位于阿拉斯加被上帝遗弃了的一个海岸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在嗜血的游牧部落中间匆匆建起几个晃晃悠悠的房屋和一个摇摇欲坠的篱笆,接着,他们就一起出发,到了灰茫茫的大海深处,追逐一条并不存在的鲸鱼。上帝已将他们遗忘了,正如路对过那家小餐馆的老板娘昨天所说的那样。
费玛清晰地看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之中,立在那个被遗弃的捕鲸人的营地上方守卫着。一根树竿的顶部挂着一盏发出微弱光亮的灯笼,灯笼在风中晃过来晃过去,在黑漆漆的荒原上忽闪着、摇曳着,而且,在北至北极、南达火地岛尖端的所有太平洋荒原上,再没有其他灯光了。一只孤零零的萤火虫。荒唐。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6]。然而,这种宝光。你的责任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让它一直亮着。在白雪覆盖的冰川脚下那片广袤的冻原深处,这盏灯绝对不能停止忽闪。防止它被狂风吹灭就是你的责任。至少是在你站岗的这段时间以及约泽尔到来之前。压根儿就不要考虑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得如何对付那些从不存在的捕鲸人,不要考虑你的近视眼、你松弛的肌肉、你软塌塌的乳房和你那臃肿笨拙又荒唐可笑的身躯。这责任就是你的。
啥意思?
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打算找一片胃灼热药片,但他并没有摸到那个小小的锡盒,而是用指头挖出了那个银耳环,银耳环闪了一闪,好像在从他后面房间照射进来的光线里着了魔一般。他将耳环抛进黑暗深处,这时他似乎听见了约珥那种挖苦的声音:
“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他面对黑夜,用一种低沉、果决的嗓音答道:
“正确。是我的问题。而且我还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暗自笑了。但这次并不是那种习惯性的自贬的苦笑,而像一个长时间地为一个复杂问题在苦苦寻求一个复杂答案却突然发现了简单答案的人一样,他吃惊得将嘴唇撮了起来。
这样想着,他转身进去了。他发现约珥和尤里·格芬促膝坐在长沙发上,在一起谈得正酣。费玛觉得,他进屋的一刹那,笑声就凝结在了他们的嘴唇上。但他并不感到嫉妒。正相反,一阵窃喜涌上他的心头,他想到自己和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女人都睡过,舒拉、尼娜和约珥。昨天还和安妮特·塔德莫。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这时,他看到迪米正跪在墙角的地毯上,一个少年老成、像个哲学家似的孩子,他用一根手指慢悠悠地转动着巴鲁赫那只内置发光系统的大地球仪。电灯光将片片海洋涂成蔚蓝色,将块块陆地涂成黄金色。小男孩是那么聚精会神,那么超脱物外,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正在做的事情上面。如同在脑子里记忆一只手提箱或是一个电闸所在位置的人一样,费玛自言自语地说,他爱这个孩子,胜于他曾爱过的任何人。包括女人。包括小男孩的母亲。包括他自己的母亲。
约珥站起身,向他走过去,似乎拿不准到底要和他握手还是只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袖子上就可以了。费玛并不等她拿定主意,而是紧紧地抱住她,将她的脑袋压在他的肩上,好像需要安慰并且理应得到安慰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她。好像他正将自己的新孤作为一件礼物送给她。约珥在他胸口咕哝了一句什么,费玛没有听清,他甚至连听都不想听,因为有个发现让他感到分外欣喜:就像本·古里安总理一样,原来约珥差不多也比他矮一个头。尽管他自己也并非高个子。
接着,约珥挣脱了他的拥抱,赶到厨房,或者说是逃到厨房,帮舒拉和特迪为众人做露馅三明治。费玛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请尤里或者茨维代表他给两位妇科大夫打个电话,把他们叫过来,还有塔马,还有,干吗不把安妮特·塔德莫也叫过来呢?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他要把所有与他新生活有关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他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打算着举行一个仪式。要向他们布道。试图告诉他们一些新闻。宣布从现在开始……不过,他或许是将丧礼和告别宴会混为一谈了。告别什么呢?他能对他们做什么样的布道呢?像他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发布呢?你们所有的人,要圣洁,为第三种状态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