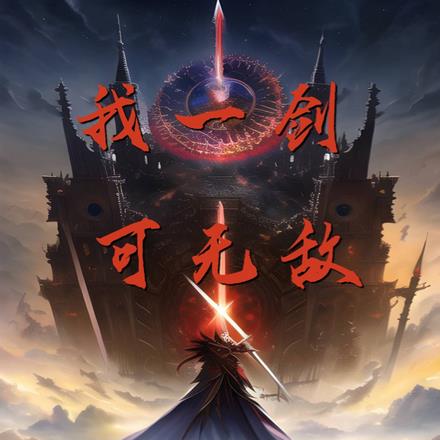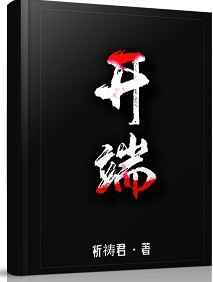戴安娜·加瓦尔东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打仗的时候。”我答道,对他的描述报以一个微笑。
他抬了抬眉毛:“越战?”
“不,二次大战时我是个战地护士,在法国战场。我见过很多那样的护士长,只用一个眼神就能把实习生和勤杂工吓得腿都软了。”之后,我得到了许多锻炼,着实利用那种不可侵犯的权威架势——姑且这么认为吧——对阵过不少比波士顿总医院的护理人员和实习生有权有势得多的人。
他专注地听着我的解释,点了点头:“是,非常合情合理。而我嘛,我用的是沃尔特·克朗凯特1。”
“沃尔特·克朗凯特?”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
他又咧开嘴,露出了那颗金牙。“你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人选?而且,我每天晚上都能免费在广播和电视上听他讲话。我曾开玩笑地跟我妈妈说——她一直想要我成为一个牧师,”他颇显沮丧地笑了笑,“我说假如那些年我在我们那边像克朗凯特那样有话直说,没准儿我早就没命上医学院了。”
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乔·艾伯纳西了。“我希望你母亲没太失望,你成了一个医生而不是牧师。”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仍旧笑着说,“我告诉她的时候,她瞅着我看了一分钟,然后大叹了一口气说:‘哎,至少我那些风湿的药你能便宜点儿给我配了。’”
我苦笑着回答:“我告诉我丈夫我想做医生的时候,连那样的热情都没有得到。他盯着我好久,最后问,如果我烦了,干吗不去养老院或监狱做义工帮人代写书信呢。”
乔注视着我,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眸有点像太妃糖,略带点金光,闪现出一丝诙谐。
“是啊,人们始终认为他们可以指着鼻子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嘿,你在这儿干吗,小女人,怎么不在家伺候老公孩子?’”他模仿道。
他无奈地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别担心,他们早晚会放弃的。现在他们多半儿不再当面问我为什么没去刷马桶了,就像我生来该做的一样。”
这时候,护士过来通知,说我的阑尾患者醒了。于是我离开了休息室,但那段从四十二页开始的友谊却发展得不错。乔·艾伯纳西从此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兴许是我身边唯一能真正了解我的选择和动机的人。
我微微一笑,感觉着封面上光滑的浮凸字体。接着我俯身向前把书放回了椅背的口袋,或许此刻我并不想逃避现实。
窗外,月光照耀下的云层把我们同下面的地球隔绝开来。云层上的一切安静、美丽而祥和,与底下混乱不安的现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有一种被当空悬挂的感觉,一动不动地缚在孤独的茧中,连身边那个女人沉重的呼吸也都混合在空调机不温不火的风声和地毯上女乘务员的脚步声之中,化成了无声的白色噪声。与此同时,我很清楚我们正无可阻挡地冲破云层,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向某个终点推进——而那个终点究竟安全与否,我们唯有期待。
我闭上眼睛,保持着休眠状态。此时的苏格兰,罗杰和布丽正在搜寻詹米。至于即将到达的波士顿,我的工作——和乔——在等着我。可詹米,他又在哪里?我努力地撇开这个念头,在做出决定之前不能去想他。
头顶感到一阵轻微的抚弄,一绺头发滑下了我的脸颊,柔和得像爱人的一个触摸。显然那无非是一股气流从头顶的排风口涌出而已,然而在我的想象之中,那浑浊的空气里的香水和烟味之下,突然有羊毛与石楠的芬芳四散开来。
<h3>让一个幽灵安歇</h3>
终回到家中,富里街的房子,我同弗兰克和布丽安娜共同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门口的杜鹃花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一簇簇枝叶疲软而破败地挂着,被烤干了的花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今年夏天很热——波士顿的夏天其实都一样——加之八月的雨水还没有到来,尽管现在已经九月中旬了。
我把行李放在大门口,继而去打开了水管的龙头。一直暴露在阳光之下,那绿色的橡皮长蛇烫手得很,我把它在手掌间焦躁地来回扔了几下,直到咕噜噜的流水瞬时间赋予了它生命,它便迅即冷却下来,喷溅出一片水花。
我从来就不太喜欢杜鹃花。要不是因为弗兰克的死,我没准儿早已把它们连根拔掉了,只是他死后,为了布丽安娜,我不想对家中的布置做任何改动。她受的打击已经够大的了,我想,在开始大学生涯的同一年里失去了父亲,她不需要更多的改变。对这所房子我已经置之不理了很长时间,完全可以继续如此。
“好了!”我愤愤地对那些杜鹃花说道,一边关上水龙头。“希望你们满意,因为你们能得到的也就这么多了。我也得去喝一杯,然后洗个澡。”看着它们沾满泥点的枝叶,我补充了一句。
我身穿晨衣坐在那巨大的下沉式浴缸边缘,看着水流轰鸣着注入其中,搅动着那泡泡浴液翻起一片芳香的浮沫。滚烫的水面上蒸汽升腾,看着有点太烫了。
我关上水——只消把水龙头迅速而利落地一拧——接着又继续坐了片刻,整幢房子静默地环绕着我,只有浴缸里一一爆破的气泡在啪啪作响,微弱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战场。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在因弗内斯登上苏格兰飞人号,感觉到脚下的铁轨隆隆地跃动起来,我便开始了这个自我测试。
我开始仔细记下途中的所有机器——所有现代生活中日常用到的点滴发明——并且,尤为重要地,一并记下我自己对它们所做出的反应。开往爱丁堡的火车、飞抵波士顿的班机、从机场叫到的出租车,以及一路上列位出席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小机械设备——自动贩卖机、路灯,还有飞机上的高空盥洗室,只消轻摁按钮,便有急漩而下的恶心的蓝绿色消毒液将排泄物与细菌一扫而尽。餐馆里,整齐地陈列着由卫生部颁发的证书,保障你在此用餐起码有较大的可能性免遭食物中毒。而我自己的家中,则有随处可见的无数按钮,提供着光照、暖气、水和煮熟的食物。
问题是——我在乎这些吗?一手伸进那热腾腾的洗澡水,我来回搅动着,望着那漩涡的阴影在大理石深处舞蹈。放弃了我习以为常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便利设施,我还能否生存?
我不断地向自己问着这个问题,每摁下一个按钮,每听到一声引擎,我已颇为确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毕竟,时间并没有改变一切。穿过这个城市,我就可能找到一些人,生活在缺少了以上很多项便利设施的环境里——远到海外,更有些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浑然不知电的存在,却依旧生活得相当满足。
对我来说,这一切我从来不太在乎。自从五岁时父母双亡,我就与兰姆叔叔,一位卓有名气的考古学家,生活在一起。因此,可以保守地用“原始”一词来形容我成长的环境,因为我一直跟随他进行所有的实地考察。的确,热水澡和电灯泡都是好东西,但没有它们的生活这辈子我也过过,并且不止一个阶段——比如战时——而我始终不认为这种缺失有多么关键。
水温降到了可以忍受的热度,我踏进浴缸,把晨衣抛在地上,脚尖上的温度使我微凉的肩头感到一阵不乏快意的震颤。
我沉入浴缸,伸展开双腿,松弛着全身上下。十八世纪的澡盆不比酒桶大多少,人们沐浴时一般分段进行,先把腿悬在澡盆之外,浸泡身体的中段,然后站起身,在浸泡双脚的同时,冲洗上半身。更多的时候,他们只用一个水壶和一个脸盆,靠洗澡巾帮忙清洗全身。
然而,方便和舒适仅仅意味着方便和舒适。它们并非生活的必需,没有它们我照样可以生存。
当然,生活的便利绝非问题的全部。那个时代是个危险四伏的地方。即使身处所谓的文明世界,其发达程度也达不到安全保障。我经历过两场重要的“现代”战争——在其中一个战场上真正地服过役——而另一场战争则每晚在我的电视机上活生生地上演着。
“文明”的战争,如果真有区别的话,比它的先前的版本要恐怖得多。战时的日常生活也许相对安全,但前提是你必须小心选择你走的道路。如今,罗克斯伯里的部分地区与两百年前我所走过的任何一条巴黎小巷同样危险。
我叹了口气,用脚趾拔起了塞子。对浴缸、炸弹和强奸犯等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臆测是毫无意义的。室内管道无非是个小小的插曲。真正的问题永远在于它所牵涉到的人。在于我、布丽安娜和詹米。
水汩汩地流尽了。我站了起来,感到有点儿头晕,随即擦干了身上最后的泡泡。大镜子上结着气雾,但还是清楚映照出我膝盖以上的人影,像只粉红色的煮熟的虾。
我扔下浴巾,开始审视自己。我把弯起的手臂举至头顶,检查有没有松垮的肌肉。没有。肱二头肌和三头肌的轮廓都很清晰,三角肌整齐、圆润地向下滑入胸大肌上方的曲线。我稍稍转向一侧,收放着腹部肌肉——内外斜肌的状况都不错,腹直肌平整到几乎有点凹陷。
“所幸我的家族没有长胖的基因。”我喃喃自语。兰姆叔叔直到七十五岁去世之时都一直保持着精干而紧致的身材。我心想,我的父亲——兰姆叔叔的兄弟——也一定是相似的身材,这么寻思着,我突然很想知道我母亲的臀部长什么样子。毕竟,女人有一定量多余的脂肪组织需要应付。
我转过身,越过肩膀朝后面照着镜子。扭转的动作让我后背上长长的柱状肌肉湿乎乎地泛起水光,我的腰身仍然存在,并且仍然颇为苗条。
至于我的臀部——“嗯,不管怎样,酒窝还没有。”我说出声来,回转身子注视着自己的身影。
“还不算太糟。”我对着镜子说。
感觉振作了一些,我穿上睡衣,开始向整幢房子道晚安。没有猫需要放出去,没有狗需要喂饱——博佐,我们最后的那条狗一年前寿终正寝了,我没有想再要一条,因为布丽安娜离家去了学校,而我自己在医院的工作时间又总是长而不规律。
我调好了温度计,检查了门窗上的锁,确保炉子上的燃具都灭了。一切就绪。十八年了,我每晚入睡前的程序都包括在布丽安娜房间里的小驻,然而自她上了大学后,这个步骤也省了。
一半出于习惯,一半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推开了她的房门,打开了灯。有些人对物品有一种别人没有的天生的感觉。布丽就是这样。她房间的墙上挂满了海报、照片、干花、扎染、证书和各种其他的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几乎都没有空隙。
有些人对布置身边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们能让每件物品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它自身的意义和它与周围物品的关系,还能传达更多——仿佛能创造一种难以定义的光环,一种既属于该物品本身又属于其不可见的主人的光环。“我存在是因为布丽安娜把我挂在了这里,”屋里的物品仿佛在如此宣告,“我存在是因为布丽安娜就是布丽安娜。”
其实,她会有这种才能有点奇怪,我心想。弗兰克也是这样,他死后我去大学办公室清理他的遗物时,我感觉那一切就好像一头灭绝了的动物留下的化石,所有的书本、纸张和零星的垃圾都完好地保持着那个曾居于此地的灵魂的形状、质感和它业已消失了的重量。
布丽安娜的有些东西很明显是属于她的——就像那些照片,我的、弗兰克的、博佐的,还有她的朋友们的。那些布料是她的创作,她选的图案,她喜欢的色彩——鲜亮的绿松石色、深沉的靛青色,还有品红色和青黄色。然而其他那些呢——为什么书桌上那堆淡水螺壳会对我说“布丽安娜”?还有那块从特鲁罗海滨带回来的圆形浮石,与千千万万块其他的浮石并无二致——唯独因为是布丽安娜捡起了它?
我对物品没有感觉。我没有想要搜罗与装饰的冲动——弗兰克常常抱怨家里斯巴达式太过简朴的家具布置,直到布丽安娜长到足以挑起这个担子的年龄。这点不知该归咎于我游牧式的成长环境呢,还是我本身的个性?那种独来独往的个性,没有任何欲望想要改变周围的环境让它来体现我的存在。
詹米也是一样。他曾随身携带一些用作工具或护身符的小物品,放在他的皮口袋里,但除此之外他既没有拥有过很多,也从未在乎过。就连我们暂居巴黎的那段奢华的日子,以及在拉里堡更长时间的平静生活,他都从未显出喜爱搜罗物品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