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就在那里打盹儿,一直打到七点。睡衣裤皱巴巴的,头发乱蓬蓬的,身上在夜间发出的汗臭味让他讨厌,于是他强迫自己下了床。在镜子前做早操这次就免了。他开始刮胡子,不过没有刮破脸。他喝了两杯咖啡。一想到果酱面包或者酸奶他就感到胃灼热。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今天早上他必须处理一件耽搁不得的事情,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为什么那么急迫。于是,他决定到楼下的信箱看看,把昨天晚上在信箱里看到的信件取出来,也要把那份报纸拿出来,但这件事所花费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然后,他将立即在书桌旁坐下来,毫不动摇地把昨天晚上没有完成的文章写完。
他打开收音机,发现新闻差不多播送完了。预计,今天白天有时晴天。沿海平原一带有零星小雨。但在北部山谷仍有严重霜冻的危险。驾驶员应被提醒注意的是,路面潮湿,要防止打滑的危险,他们被请求注意减速慢行,尽量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
他们都怎么啦?费玛咕哝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少管闲事呢?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司机?北部山谷的农夫?沿海平原游泳的人?在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应当说“我请求,我提醒”时,我们为什么要被请求、被提醒呢?全疯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但他们却在为霜冻的危险担忧。事实上,只有急刹车加上急转弯或许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灾难。甚至连这样做都非常让人怀疑。
费玛关掉收音机,接着就给安妮特·塔德莫打电话:他还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向她道歉呢。至少,他应该对她的安康表现出一些兴趣。说不定她丈夫已经听够了意大利小歌剧,在深更半夜忐忑不安地回来了,拖着两三只行李箱,一边跪到地上,亲吻着她的双脚。她会不会把他俩发生的事情向他坦白了呢?那个做丈夫的有可能拿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在我眼前吗?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由于早晨他脑子糊涂,费玛误拨了茨维·克鲁泡特金家的号码。茨维格格直笑,他说,事实上,他这会儿正在刮胡子,刚刮了一半,但他刚才还在心里问自己,费玛今天早上这是怎么啦?他把我们都忘啦?费玛没有听出茨维的话中暗藏着讥讽。
“你是什么意思,茨维卡?我自然是没有忘记你。我绝对不会。我只不过想着要改变一下,我不应该一大早就给你打电话。你知道,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我或许还是有点希望的。”
克鲁泡特金保证五分钟之后就给他打过去,一刮完胡子就打过去。
半小时之后,费玛把自尊吞到肚子里,又给茨维拨了过去:
“喂,是谁忘了谁呀?你能否给我两三分钟时间?”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说,他昨天晚上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了今天早上他就连自己还要不要坚持昨天晚上的观点都没有了把握,他想听听他的意见。问题是这样的:两天前的《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君特·格拉斯[1]在柏林给学生演讲的报道。那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很有分量的演讲。格拉斯首先谴责纳粹统治时期,接着就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行和希特勒的种种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把以色列和南非放在一起所做的比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费玛,”茨维说,“这篇报道我读过。我们前天还在一起讨论过呢。快切入正题吧。把你的问题解释给我听听。”
“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了。”费玛说,“但首先,你给我解释一件事情,茨维卡。为什么这个格拉斯坚持把纳粹分子称作‘他们’?可是这些年来,你也好,我也好,只要写到军事占领、价值沦丧、占领地上的反抗,甚至是黎巴嫩战争,我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我们’这样的代词。格拉斯实际上还在纳粹国防军当过兵!和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是海因里希·伯尔[2]。他每天早晨和其他人一样,都得行纳粹军礼,高喊‘哈依,希特勒!’然而现在,他却称他们为‘他们’。而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黎巴嫩的人,一个从没有在占领地服过兵役、双手自然绝对比君特·格拉斯洁净的人,却常常说的是‘我们’、写的是‘我们’。‘我们的罪过’。甚至还有‘我们白流了的鲜血’。这个‘我们’是什么?是从独立战争[3]遗留下来的东西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帕尔马赫。[4]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和莱文杰拉比[5]吗?你和卡亨拉比[6]吗?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教授?也许你、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仿效格拉斯和伯尔的时候到了。也许,从现在起,我们都应该无一例外地、自觉自愿地、铿锵有力地说:‘他们’。你是怎么想的?”
“听着,”茨维·克鲁泡特金疲惫地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这就是给你的解答。”
“你疯了吗?”费玛勃然大怒地插进来,“你能听见你这会儿在说些什么吗?你说,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一切’到底他妈的指什么?根据你的说法,那件在柏林已经结束了,但仍在耶路撒冷发生着的事,你讲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教授?你正在做的是把我们和他们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你言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你自己就可以看看,茨维卡,掉入陷阱有多么容易呀。你看看我们不得不在上面行走的绳索有多细呀。”
“冷静些,费玛。”茨维·克鲁泡特金向他发出了哀求,尽管费玛已经冷静下来了,“这会儿才八点呢。你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说话?你哪天晚上干脆过来好了。到时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我这里有一些法国产的拿破仑白兰地。是舒拉的姐姐带回来的。但是这一周不行。本学期快要结束了,我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准备培养我当系主任。下个星期你过来好吗?费玛,听上去你不太舒服,费玛,还有,尼娜刚才还在和舒拉说你又有些消沉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
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一切正常。我在听着呢。”
原来,老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给他找到了一些工匠,工匠下周就可以来,给他的公寓墙重新抹泥灰、粉刷。“他们都是阿布迪斯村的阿拉伯人,所以根据你的口味,这是绝对的可食[11],埃弗雷姆。”这番话让老人想起了一个迷人的哈西德派故事。根据犹太传说,天堂上的义人能够允许在吃利维坦[12]还是吃野牛上随便选择,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或许总有那么一个极端挑剔的犹太人,他坚持要吃鱼,因为他不能依靠上帝本人的饮食规定来生活。
接着,他给费玛解释这个笑话的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到最后,费玛甚至觉得父亲身上那股特别的气味已经通过电话线传进了自己的鼻孔:那是一种东欧的鸡尾酒气味,将一股淡淡的香气和没有晾晒的被子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种胡萝卜烧鱼的味道和黏绵的烈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又为这种反感觉得羞愧,他又产生了由来已久的冲动,他要向父亲挑衅,挑战一切他认为神圣的东西,直到他大为光火。他说:
“听着,爸爸。仔细地听着。首先,说说阿拉伯人。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上千次了,他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你难道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在可食和不可食的问题上,也不在地狱和天堂的问题上。这只不过是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巴鲁赫立即表示同意。
“毋庸置疑,”他用诵读《塔木德》[13]的那种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没人会否认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除了阿拉伯人他们自己,费姆奇卡,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表现并不像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人的表现。”
费玛顿时忘记了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父亲进行政治辩论的神圣誓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那里动情地对父亲解释说,我们绝不能像一个喝得烂醉的乌克兰马车夫,当他的马不再驯服地为他拉车时,就抽打自己的马,直到把畜生给打死了。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难道是我们的役马吗?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他们会一直为我们劈柴、汲水,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你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子子孙孙地扮演我们家奴的角色?他们难道不也是人吗?如今,每一个赞比亚和冈比亚都独立了,所以,为什么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也还要在那里默默地擦洗我们的茅房、打扫我们的街道、刷洗我们餐馆里的盘子、擦拭我们老人病房里老年人的屁眼,之后还要说‘谢谢您’?如果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为我们犹太人规划了这样的一个未来,你会作何感想?”
“家奴”这个词,要么也许是“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让老人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就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上。和平常一样,讲述完了之后他总要拖泥带水地附上一长串解释和道德寓意。
最后,费玛绝望地放弃了,他喊了起来,他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装修的工匠,巴鲁赫你他妈的不要老是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不要给他补贴,不要给他的墙壁抹灰泥,不要给他介绍配偶。“你可能忘记了,爸,可我今年碰巧已经五十四岁了!”
费玛喊完之后,老人平和地说道:
“很好,亲爱的。很好。看来我过去的想法是错了。我犯罪了,我犯错误了,我离开道路了。既然这样,我还将尽力为你找一个手艺高超的犹太装修工。一个没有任何利用殖民地劳动力污点的人。假如这样的完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话。”
“说到点子上去了。”费玛得意地欢呼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国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一个犹太建筑师,或者是男性护士,或者是园丁。这就是你们占领地对复国梦所干的好事!阿拉伯人在为我们建设国土,而我们却坐在那里,大吃特吃利维坦和野牛。然后,我们就出去杀他们,还杀他们的孩子,只因为他们心存抱怨,不为弥赛亚到来之前上帝选民所享受的源源不断的特权觉得幸福和感激。”
“弥赛亚,”巴鲁赫忧伤地说,“说不定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也许只是因为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优秀人物他才没让我们大家知道。我这儿有个故事,说的是斯特里斯克的尤里先生,那个神圣的撒拉弗[14],著名诗人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5]的爷爷,有一次,他在森林里溜达,结果迷路了……”
“那就让他溜达好了!”费玛打断了父亲的话,“让他永远地迷失在那里吧!还有他的孙子。还有弥赛亚,你也不要再说关于他的什么屁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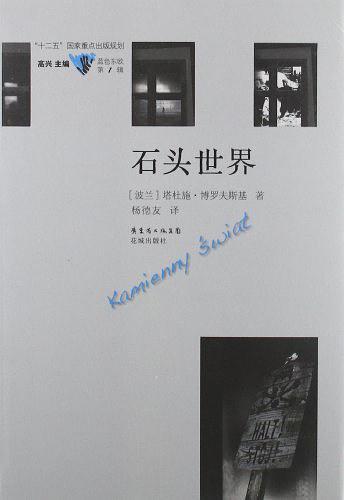


![豪门阔太只想离婚[穿书]](https://jmvip3.com/images/14561/42181fd081822ce10202233d8793d78c.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