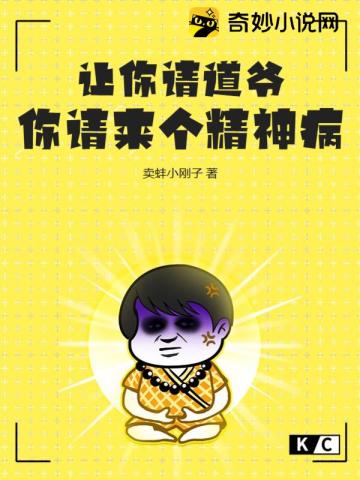张爱玲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卍字栏干,栏干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彷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纤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袴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
薇龙对着玻璃门扯扯衣襟,理理头发。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现在,这一类的「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她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她对于她那白净的皮肤,原是引为憾事的,一心想晒黑它,使它合于新时代的健康美的标准。但是她来到香港之后,眼中的粤东佳丽大都是橄榄色的皮肤。她在南英中学读书,物以希为贵,倾倒于她的白的,大不乏人;曾经有人下过这样的考语: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薇龙端相着自己,这句「非礼之言」蓦地兜上心来。她把眉毛一皱,掉过身子去,将背倚在玻璃门上。
姑母这里的娘姨大姐们,似乎都是俏皮人物,糖醋排骨之流,一个个拖着木屐,在走廊上踢托踢托地串来串去。这时候便听到一个大姐娇滴滴地叫道:「睇睇,客厅里坐的是谁?」睇睇道:「想是少奶娘家的人。」听那睇睇的喉咙,想必就是适才倒茶的那一个,长脸儿,水蛇腰;虽然背后一样的垂着辫子,额前却梳了虚笼笼的鬅头。薇龙肚里不由的纳罕起来,那「少奶」二字不知指的是谁?没听说姑母有子嗣,哪儿来的媳妇?难不成是姑母?姑母自从嫁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就和薇龙的父亲闹翻了,不通庆吊,那时薇龙还没出世呢。但是常听家人谈起,姑母年纪比父亲还大两岁,算起来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如何还称少奶,想必那女仆是伺候多年的旧人,一时改不过口来?正在寻思,又听那睇睇说道:「真难得,我们少奶起这麽一大早出门去!」那一个鼻里哼了一声道:「还不是乔家十三少爷那鬼精灵,说是带她到浅水湾去游泳呢!」睇睇哦了一声道:「那,我看今儿指不定什麽时候回来呢。」那一个道:「可不是,游完水要到丽都去吃晚饭,跳舞。今天天没亮就催我打点夜礼服、银皮鞋,带了去更换。」睇睇悄悄地笑道:「乔家那小子,呕人也呕够了!我只道少奶死了心,想不到他那样机灵人,还是跳不出她的手掌心去!」那一个道:「罢了!罢了!少嚼舌头,里面有人。」睇睇道:「叫她回去罢。白叫人家獃等着,作孽相!」那一个道:「理她呢!你说是少奶娘家人,想必是打抽丰的,我们应酬不了那麽多!」睇睇半天不做声,然后细着嗓子笑道:「还是打发她走罢,一会儿那修钢琴的俄罗斯人要来了。」那一个听了,格格地笑了起来,拍手道:「原来你要腾出这间屋子来和那亚历山大?阿历山杜维支鬼混!我道你为什麽忽然婆婆妈妈的,一片好心,不愿把客人乾搁在这里。果然里面大有道理。」睇睇赶着她便打,只听得一阵劈啪,那一个尖声叫道:「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睇睇也嗳唷连声道:「动手的是小人,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真踢起人来了!」一语未完,门开处,一只朱漆描金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的溜溜地飞了进来,不偏不倚,恰巧打中薇龙的膝盖,痛得薇龙弯了腰直揉腿。再抬头看时,一个黑里俏的丫头,金鸡独立,一步步跳了进来,踏上那木屐,扬长自去了,正眼也不看薇龙一看。
薇龙不由得生气,再一想:「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这就是求人的苦处。看这光景,今天是无望了,何必赖在这里讨人厌?只是我今天大远的跑上山来,原是扯了个谎,在学校里请了假来的,难道明天再逃一天学不成?明天又指不定姑母在家不在。这件事,又不是电话里可以约好面谈的!踌躇了半晌,方道:「走就走罢!」出了玻璃门,迎面看见那睇睇斜倚在石柱上,搂起袴脚来搥腿肚子,踢伤的一块还有些红红的。那黑丫头在走廊尽头探了一探脸,一溜烟跑了。睇睇叫道:「睨儿你别跑!我找你算帐!」睨儿在那边笑道:「我哪有那麽多的工夫跟你胡闹?你爱动手动脚,等那俄国鬼子来跟你动手动脚好了。」睇睇虽然喃喃骂着小油嘴,也掌不住笑了;掉转脸来瞧见薇龙,便问道:「不坐了?」薇龙含笑点了点头道:「不坐了,改天再来;难为你陪我到花园里去开一开门。」
两人横穿过草地,看看走近了那盘花绿漆的小铁门。香港地气潮湿,富家宅第大都建筑在三四丈高的石基上,因此出了这门,还要爬下螺旋式的百级台阶,方才是马路。睇睇正在抽那门闩,底下一阵汽车喇叭响,睨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斜刺里掠过薇龙睇睇二人,蹬蹬蹬跑下石级去,口里一路笑嚷:「少奶回来了!少奶回来了!」睇睇耸了耸肩冷笑道:「芝麻大的事,也值得这样舍命忘身的,抢着去拔个头筹!一般是奴才,我却看不惯那种下贱相!」一扭身便进去了。丢下薇龙一个人呆呆站在铁门边;她被睨儿乱哄哄这一阵搅,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的发了慌。扶了铁门望下去,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开车的看不清楚,似乎是个青年男子,伸出头来和她道别,她把脖子一僵,就走上台阶来了。
睨儿早满面春风迎了上去问道:「乔家十三少爷怎麽不上来喝杯啤酒?」那妇人道:「谁有空跟他歪缠?」睨儿听她声气不对,连忙收起笑容,接过她手里的小藤箱,低声道:「可该累着了!回来得倒早!」那妇人回头看汽车已经驶开了,便向地上重重地啐了一口,骂道:「去便去了,你可别再回来!我们是完了!」睨儿看她是真动了大气,便不敢再插嘴。那妇人瞅了睨儿一眼,先是不屑对她诉苦的神气,自己发了一会愣,然后鼻子里酸酸地笑了一声道:「睨儿你听听,巴巴的一大早请我到海边去,原来是借我做幌子呢。他要约玛琳赵,她们广东人家规矩严,怕她父亲不答应,有了长辈在场监督,赵家的千金就有了护身符。他打的这种主意,亏他对我说得出口!」睨儿忙不迭跌脚叹息,骂姓乔的该死。
那妇人且不理会她,透过一口气来接下去说道:「我替人拉拢是常事,姓乔的你不该不把话说明白了,作弄老娘。老娘眼睛里瞧过的人就多了,人人眼睛里有了我就不能有第二个人。唱戏唱到私订终身后花园,反正轮不到我去扮奶妈!吃酒,我不惯做陪客!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你这猴儿崽子,胆大包天,到老娘面前捣起鬼来了!」一面数落着,把面纱一掀,掀到帽子后头去,移步上阶。
薇龙这才看见她的脸,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薇龙心里一震,脸上不由热辣辣起来。再听睨儿跟在姑母后面问道:「乔家那小子再俏皮也俏皮不过您。难道您真陪他去把赵姑娘接了出来不成?」那妇人这才眉飞色舞起来,道:「我不见得那麽傻!他在汽车上一提议,我就说:『好吧,去接她,但是三个人怪僵的,你再去找一个人来。』他倒赞成,可是他主张先接了玛琳赵再邀人,免得二男二女,又让赵老爷瞎疑心。我说:「我们顺手牵羊,拉了赵老太爷来,岂不是好?我不会游泳,赵老太爷也不会,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有个伴儿。」姓乔的半天不言语,末了说:「算了罢!还是我们两个人去清静些。」我说:「怎麽啦?」他只闷着头开车;我看看快到浅水湾了,推说中了暑,逼着他一口气又把车开了回来,累了他一身大汗,要停下来喝瓶汽水,我也不许,总算出了一口气。」
睨儿拍手笑道:「真痛快!少奶摆布得他也够了!只是一件,明儿请客,想必他那一份帖子是取消了,还得另找人补缺吧?请少奶的示。」那妇人偏着头想了一想道:「请谁呢?这批英国军官一来了就算计我的酒,可是又不中用,喝多了就烂醉如泥。哦!你给我记着,那陆军中尉,下次不要他上门了,他喝醉了尽黏着睇睇胡调,不成体统!」睨儿连声答应着。那妇人又道:「乔诚爵士有电话来没有?」睨儿摇了摇头笑道:「我真是不懂了;从前我们爷在世,乔家老小三代的人,成天电话不断,鬼鬼祟祟地想尽方法,给少奶找麻烦,害我们底下人心惊肉跳,只怕爷知道了要恼。如今少奶的朋友都是过了明路的了,他们反而一个个拿班做势起来!」那妇人道:「有什麽难懂的?贼骨头脾气罢了!必得偷偷摸摸的,才有意思!」睨儿道:「少奶再找个合适的人嫁了,不怕他们不眼红!」那妇人道:「呸!又讲獃话了。我告诉你──」说到这里,石级走完了,见铁门边有生人,便顿住了口。
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颏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麽?」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麽?」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的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赔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麽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睨儿在旁,见她窘得下不来台,心有不忍,笑道:「人家还没有开口,少奶怎麽知道人家是借钱来的?可是古话说的,三年前被蛇蛟了,见了条绳子也害怕!葛姑娘您有所不知,我们公馆里,一年到头,川流不息的有亲戚本家同乡来打抽丰,少奶是把胆子吓细了。姑娘您别性急,大远地来探亲,娘儿俩也说句体己话儿再走。你且到客厅里坐一会,让我们少奶歇一歇,透过这口气来,我自会来唤你。」梁太太淡淡的一笑道:「听你这丫头,竟替我赔起礼来了。你少管闲事罢!也不知你受了人家多少小费!」睨儿道:「呵哟!就像我眼里没见过钱似的!你看这位姑娘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只怕还买不动我呢!」睨儿虽是一片好意给薇龙解围,这两句话却使人难堪,薇龙勉强微笑着,脸上却一红一白,神色不定。睨儿又凑在梁太太耳朵边唧唧哝哝说道:「少奶,你老是忘记,美容院里冯医生嘱咐过的,不许皱眉毛,眼角容易起鱼尾纹。」梁太太听了,果然和颜悦色起来。睨儿又道:「大毒日头底下站着,仔细起雀斑!」一阵风把梁太太撮哄到屋里去了。
薇龙一个人在太阳里立着,发了一回獃,腮颊晒得火烫;滚下来的两行泪珠,更觉得冰凉的,直凉进心窝里去。抬起手背来揩了一揩,一步懒似一步地走进回廊,在客室里坐下。心中暗想:「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乾净,我只道是造谣言的人有心糟蹋寡妇人家,再加上梁季腾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阔人,姑母又是他生前的得意人儿,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注现款给她,房产在外,眼红的人多,自然更说不出好话来。如今看情形,竟是真的了!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再行考虑一下。可是这麽一来,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把方才那一幕细细一想,不觉又心酸起来。
葛家虽是中产之家,薇龙却也是娇养惯的,哪里受过这等当面抢白,自己正伤心着,隐隐地听得那边屋里有人高声叱骂,又有人摔门,又有人抽抽咽咽地哭泣。一个小丫头进客厅来收拾喝残了的茶杯,另一个丫头便慌慌张张跟了进来,扯了扯她的袖子,问道:「少奶和谁发脾气?」这一个笑道:「骂的是睇睇,要你吓得这样做什麽?」那一个道:「是怎样闹穿的?」这一个道:「不仔细。请乔诚爵士请不到,查出来是睇睇陪他出去过几次,人家乐得叫她出去,自然不必巴巴的上门来挨光了。」她们叽叽咕咕说着,薇龙两三句中也听到了一句。只见两人端了茶碗出去了。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花背后门帘一动,睨儿笑嘻嘻走了出来。薇龙不觉打了个寒噤。睨儿向她招了招手,她便跟着走进穿堂。睨儿低声笑道:「你来得不巧,紧赶着少奶发脾气。回来的时候,心里就不受用,这会儿又是家里这个不安分的,犯了她的忌,两面夹攻,害姑娘受了委屈。」
薇龙笑道:「姐姐这话说重了!我哪里就受了委屈?长辈奚落小孩子几句,也是有的,何况是自己姑妈,骨肉至亲?就打两下也不碍什麽。」睨儿道:「姑娘真是明白人。」一引把她引进一间小小的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几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那种古色古香的绫子,薇龙这一代人,除了做被面,却是少见。地下搁着一只二尺来高的景泰蓝方罇,插的花全是小白嗗嘟,粗看似乎晚香玉,只有华南住久的人才认识是淡巴菰花。
薇龙因为方才有那一番疑虑,心里打算着,来既来了,不犯着白来一趟,自然要照原来计划向姑母提出要求,依不依由她。她不依,也许倒是我的幸运。这麽一想,倒坦然了。四下里一看,觉得这间屋子,俗却俗得妙。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她头上的帽子已经摘了下来,家常扎着一条鹦哥绿包头,薇龙忍不住要猜测,包头底下的头发该是什麽颜色的,不知道染过没有?薇龙站在她跟前,她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磕在脸上,彷佛是睡着了。
薇龙趔趄着脚,正待走开,梁太太却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道:「你坐!」以后她就不言语了,好像等着对方发言。薇龙只得低声下气说道:「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我这都是实话:两年前,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我们一家大小避到香港来,我就进了这儿的南英中学。现在香港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涨,我爸爸的一点积蓄,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同时上海时局也缓和了下来,想想还是回上海。可是我自己盘算着,在这儿书念得好好的,明年夏天就能够毕业了,回上海,换学堂,又要吃亏一年。可是我若一个人留在香港,不但生活费要成问题,只怕学费也出不起了。我这些话闷在肚子里,连父母面前也没讲;讲也是白讲,徒然使他们发愁。我想来想去,还是来找姑妈设法。」
梁太太一双纤手,搓得那芭蕉扇柄的溜溜地转,有些太阳光从芭蕉筋纹里漏进来,在她脸上跟着转。她道:「小姐,你处处都想到了,就是没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就是愿意帮忙,也不能帮你的忙;让你爸爸知道了,准得咬我诱拐良家女子。我是你家什麽人?──自甘下贱,败坏门风,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吓!越是破落户,越是茅厕里砖头,又臭又硬。你生晚了,没赶上热闹,没听得你爸爸当初骂我的话哩!」薇龙道:「爸爸就是这书獃子脾气,再劝也改不了。说话又不知轻重,难怪姑妈生气。可是事隔多年,姑妈是宽宏大量的,难道还在我们小孩子身上计较不成?」梁太太道:「我就是小性儿!我就是爱嚼这陈谷子烂芝麻!我就是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她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
薇龙赔笑道:「姑妈忘不了,我也忘不了。爸爸当初造了口舌上的罪过,姑妈得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以后慢慢地报答您!」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筋纹,撕了又撕。薇龙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挡着脸,原来是从扇子的漏缝里盯眼看着自己呢!不由得红了脸。梁太太的手一低,把扇子徐徐叩着下颏,问道:「你打算住读?」薇龙道:「我家里搬走了,我想我只好住到学校里去。我打听过了,住读并不比走读贵许多。」梁太太道:「倒不是贵不贵的话。你跟着我住,我身边多个人,陪着我说说话也好。横竖家里有汽车,每天送你上学,也没有什麽不便。」薇龙顿了一顿方道:「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梁太太道:「只是一件,你保得住你爸爸不说话麽?我可担不起这离间骨肉的罪名。」薇龙道:「我爸爸若有半句不依,我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见姑妈。」梁太太格格笑道:「好罢!我随你自己去编个谎哄他。可别圆不了谎!」薇龙正待分辩说不打算扯谎,梁太太却岔开问道:「你会弹钢琴麽?」薇龙道:「学了两三年;可是手笨,弹得不好。」梁太太道:「倒也不必怎样高明,拣几支流行歌曲练习练习,人人爱唱的,能够伴奏就行了。英国的大户人家小姐都会这一手,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我看你爸爸那古董式的家教,想必从来不肯让你出来交际。他不知道,就是你将来出了阁,这些子应酬工夫也少不了的,不能一辈子不见人。你跟着我,有机会学着点,倒是你的运气。」
她说一句,薇龙答应一句。梁太太又道:「你若是会打网球,我练习起来倒有个伴儿。」薇龙道:「会打。」梁太太道:「你有打网球的衣服麽?」薇龙道:「就是学校里的运动衣。」梁太太道:「恶!我知道,老长的灯笼裤子,怪模怪样的,你拿我的运动衣去试试尺寸,明天裁缝来了,我叫他给你做去。」便叫睨儿去寻出一件鹅黄丝质衬衫,鸽灰短袴;薇龙穿了觉得太大,睨儿替她用别针把腰间摺了起来。梁太太道:「你的腿太瘦了一点,可是年轻的女孩子总是瘦的多。」薇龙暗暗担着心事,急欲回家告诉父母,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于是匆匆告了辞,换了衣服,携了阳伞,走了出来,自有小丫头替她开门。睨儿特地赶来,含笑挥手道:「姑娘好走!」那一份儿殷勤,又与前不同了。
薇龙沿着路往山下走,太阳已经偏了西,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乾黄松鬈,像雪茄烟丝。南方的日落是快的,黄昏只是一刹那。这边太阳还没有下去,那边,在山路的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的,早有一撇月影儿。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彷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窠。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
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薇龙这麽想着:「至于我,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她那天回去仔细一盘算,父亲面前,谎是要扯的,不能不和母亲联络好了,上海方面埋个伏线,声气相通,谎话戳穿的机会少些。
主意打定,便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她怎样去见了姑母,姑母怎样答应供给学费,并留她在家住,却把自己所见所闻梁太太的家庭状况略过了。
她母亲虽然不放心让她孤身留在香港,同时也不愿她耽误学业。姑太太从前闹的那些话柄子,早已事过境迁,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久之也就为人淡忘了。如今姑太太上了年纪,自然与前不同,这次居然前嫌冰释,慷慨解囊,资助侄女儿读书,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薇龙的母亲原说要亲身上门去道谢,薇龙竭力拦住了,推说梁太太这两天就要进医院割治盲肠,医生吩咐静养,姑嫂多年没见面,一旦会晤,少不得有一番痛哭流涕,激动了情感,恐怕于病体不宜。葛太太只得罢了,在葛豫琨跟前,只说薇龙因为成绩优良,校长另眼看待,为她捐募一个奖学金,免费住读。葛豫琨原是个不修边幅的名士脾气,脱略惯了,不像他太太一般的讲究礼数,听了这话,只夸赞了女儿两句,也没有打算去拜见校长,亲口谢他造就人才的一片苦心。
葛家老夫妇归心似箭,匆匆整顿行装,回掉了房子。家里只有一个做菜的老妈子,是在上海用了多年的,依旧跟着回上海去。另一个粗做的陈妈是在香港雇的,便开销了工钱打发她走路。薇龙送了父母上船,天已黑了下来,陈妈陪着她提了一只皮箱,向梁太太家走去。
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地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梁家在这条街上是独门独户,柏油山道上空落落,静悄悄地,却排列着一行汽车。薇龙暗道:「今天来得不巧,姑妈请客,哪里有时间来招呼我?」一路拾级上阶,只有小铁门边点了一盏赤铜攒花的仿古宫灯。人到了门边,依然觉得门里鸦雀无声,不像是有客,侧耳细听,方才隐隐听见清脆的洗牌声,想必有四五桌麻将。
香港的深宅大院,比起上海的紧凑、摩登,经济空间的房屋,又另有一番气象。薇龙正待揿铃,陈妈在背后说道:「姑娘仔细有狗!」一语未完,真的有一羣狗齐打伙儿一递一声叫了起来。陈妈着了慌,她身穿一件簇新蓝竹布罩褂,浆得挺硬。人一窘便在蓝布褂里打旋磨,擦得那竹布淅沥沙啦响。她和梁太太家的睇睇和睨儿一般的打着辫子,她那根辫子却紥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盘!因道:「陈妈你去吧!再耽搁一会儿,山上走路怪怕的。这儿两块钱给你坐车。箱子就搁在这儿,自有人拿。」把陈妈打发走了,然后揿铃。
小丫头通报进去,里面八圈牌刚刚打完,正要入席。梁太太听说侄小姐来了,倒踌躇了一下。她对于银钱交易,一向是仔细的,这次打算在侄女儿身上大破悭囊,自己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这笔学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好在钱还没有过手,不妨趁今晚请客的机会,叫这孩子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俗语道:「真金不怕火烧。」自然立见分晓。只是一件,今天在座的男女,都是配好了搭子的,其中布置,煞费苦心。若是这妮子果真一鸣惊人,雏凤清于老凤声,势必引起一番骚动,破坏了均衡。若是薇龙不济事的话,却又不妙,盛会中夹着个木头似的孩子,更觉扫兴;还有一层,眼馋的人太多了。梁太太瞟了一瞟她迎面坐着的那个乾瘦小老儿,那是她全盛时代无数的情人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名唤司徒协,是汕头一个小财主,开有一家搪瓷马桶工厂。梁太太交游虽广,向来偏重于香港的地头蛇,带点官派的绅士阶级,对于这一个生意人之所以恋恋不舍,却是因为他知情识趣,工于内媚。二人相交久了,梁太太对于他竟有三分怕惧,凡事碍着他,也略存顾忌之心。司徒协和梁太太,二十年如一日,也是因为她摸熟了自己的脾气,体贴入微,并且梁太太对于他虽然不倒贴,却也不需他破费,借她地方请请客,场面既漂亮,应酬又周到,何乐而不为。今天这牌局,便是因为司徒协要回汕头去嫁女儿,梁太太为他饯行。他若是看上了薇龙,只怕他就回不了汕头,引起种种枝节。
梁太太因低声把睨儿唤了过来,吩咐道:「你去敷衍敷衍葛家那孩子,就说我这边分不开身,明天早上再见她。问她吃过了晚饭没有?那间蓝色的客房,是拨给她住的,你领她上去。」睨儿答应着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袴,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娬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麽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羣客,」又附耳道:「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们,少奶怕你跟他们谈不来,僵得慌,叫给姑娘另外开一桌饭,在楼上吃。」薇龙道,「多谢,我吃过了饭来的。」睨儿道:「那麽我送您到您房间里去罢。夜里饿了,您尽管揿铃叫人送夹心面包上来,厨房里直到天亮不断人的。」
薇龙上楼的时候,底下正入席吃饭,无线电里乐声悠扬,薇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那盏半旧的红纱壁灯似乎摇摇晃晃,人在屋里,也就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薇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阑干外浩浩荡荡都是雾,一片蒙蒙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薇龙打开了皮箱,预备把衣服腾到抽屉里,开了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不觉咦了一声道:「这是谁的?想必是姑妈忘了把这橱腾空出来。」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却都合身,她突然省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麽多?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麽分别?」坐了一会,又站起身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衣服的脇下原先挂着白缎子小荷包,装满了丁香花末子,薰得满橱香喷喷的。
薇龙探身进去整理那些荷包,突然听见楼下一阵女人的笑声,又滑又甜,自己也掌不住笑了起来道:「听那睨儿说,今天的客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老爷们是否上了年纪,不得而知,太太们呢,不但不带太太气,连少奶奶气也不沾一些!」楼下吃完了饭,重新洗牌入局,却分了一半人开留声机跳舞。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想到这里,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看看也好!」她说这话,只有嘴唇动着,并没有出声。然而她还是探出手来把毯子拉上来,蒙了头,这可没有人听得见了。她重新悄悄说道:「看看也好!」便微笑着入睡。
第二天,她是起早惯了的,八点钟便梳洗完毕下楼来。那时牌局方散,客室里烟烟气花气人气,混沌沌地,睨儿监督着小丫头们收拾糖果盆子。梁太太脱了鞋,盘腿坐在沙发上抽烟,正在骂睇睇呢。睇睇斜签靠在牌桌子边,把麻将牌慢吞吞地掳了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丢在紫檀盒子里,唏哩哗啦一片响。梁太太扎着夜蓝绉纱包头;耳边露出两粒钻石坠子,一闪一闪,像是挤着眼在笑呢;她的脸却铁板着。见薇龙进来,便点了一个头,问道:「你几点钟上学去?叫车夫开车送你去。好在他送客刚回来,还没睡。」薇龙道:「我们春假还没完呢。」梁太太道:「是吗?……不然,今儿咱们娘儿俩好好的说会子话,我这会子可累极了。睨儿,你给姑娘预备早饭去。」说完了这话,便只当薇龙不在跟前,依旧去抽她的烟。
睇睇见薇龙来了,以为梁太太骂完了,端起牌盒子就走。梁太太喝道:「站住!」睇睇背向着她站住了。梁太太道:「从前你和乔琪乔的事,不去说它了。骂过多少回了,只当耳边风!现在我不准那小子上门了,你还偷偷摸摸的去找他。打量我不知道呢!你就这样贱,这样的迁就他!天生的丫头坯子!」睇睇究竟年纪轻,当着薇龙的面,一时脸上下不来,便冷笑道:「我这样的迁就他,人家还不要我呢!我并不是丫头坯子,人家还是不敢请教。我可不懂为什麽!」梁太太跳起身来,唰的给了她一个巴掌。睇睇索性撒起泼来。嚷道:「还有谁在你跟前捣鬼呢?无非是乔家的汽车夫。乔家一门子老的小的,你都一手包办了,他家七少奶奶新添的小少爷,只怕你早下了定了。连汽车夫你都放不过。你打我!你只管打我!可别叫我说出好的来了!」梁太太坐下身来,反倒笑了,只道:「你说!你说!说给新闻记者听去。这不花钱的宣传,我乐得塌个便宜。我上没有长辈,下没有儿孙,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朋友,我怕谁?你趁早别再糊涂了。我当了这些年的家,不见得就给一个底下人叉住了我。你当我这儿短不了你麽?」
睇睇返身向薇龙溜了一眼,撇嘴道:「不至于短不了我哇!打替工的早来了。这回子可趁了心了,自己骨血,一家子亲亲热热的过活罢,肥水不落外人田。」梁太太道:「你又拉扯上旁人做什麽?嘴里不乾不净的!我本来打算跟你慢慢的算帐,现在我可太累了,没这精神跟你歪缠。你给我滚!」睇睇道:「滚就滚!在这儿做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梁太太道:「你还打算有出头之日呢!只怕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你以为你在我这里混过几年,认得几个有大来头的人,有了靠山了。我叫你死了这条心!港督跟前我有人;你从我这里出去了,别想在香港找得到事。谁敢收容你!」睇睇道:「普天下就只香港这豆腐乾大一块地麽?」梁太太道:「你跑不了!你爹娘自会押你下乡去嫁人。」睇睇哼了一声道:「我爹娘管得住我麽?」梁太太道:「你娘又不傻。她还有七八个女儿求我提拔呢。她要我照应你妹妹们,自然不敢不依我的话,把你带回去严加管束。」睇睇这才呆住了,一时还体会不到梁太太的意思;獃了半晌,方才顿脚大哭起来。睨儿连忙上前半推半搡把她运出了房,口里数落道:「都是少奶把你惯坏了,没上没下的!你知趣些;少奶气平了,少不得给你办一份嫁妆。」
睨儿与睇睇出了房,小丫头便蹑手蹑脚钻了进来,送拖鞋给梁太太,低声道:「少奶的洗澡水预备好了。这会儿不早了,可要洗了澡快上床歇歇?」梁太太趿上了鞋,把烟卷向一盆杜鹃花里一丢,站起身来便走。那杜鹃花开得密密层层的,烟卷儿窝在花瓣子里,一霎时就烧黄了一块。
薇龙一个人在那客室里站了一会,小丫头来请她过里间去吃早饭;饭后她就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又站在窗前发呆。窗外就是那块长方形的草坪,修剪得齐齐整整,洒上些晓露,碧绿的,绿得有些牛气。有只麻雀,一步一步试探着用八字脚向前走,走了一截子,似乎被这愚笨的绿色大陆给弄糊涂了,又一步一步走了回来。薇龙以为麻雀永远是跳着的,想不到牠还会踱方步,倒看了半晌,也许那不是麻雀?正想着,花园的游廊里走出两个挑夫,担了一只朱漆箱笼,哼哼呵呵出门去了,后面跟着一个身穿黑拷绸衫袴的中年妇人,想是睇睇的娘。睇睇也出来了,立在当地,似乎在等着屋里其他的挑夫;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脸上薄薄的抹上一层粉,变为淡赭色。薇龙只看见她的侧影,眼睛直瞪瞪的,一点面部表情也没有,像泥制的面具。看久了,方才看到那寂静的面庞上有一条筋在那里缓缓地波动,从腮部牵到太阳心──原来她在那里吃花生米呢,红而脆的花生米衣子,时时在嘴角掀腾着。
薇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掉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衣橱里黑沉沉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可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她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对于她,不过是炫弄衣服的机会罢了。她暗自庆幸,梁太太只拿她当个幌子,吸引一般年轻人,难得带她到上等舞场去露几次脸,总是家里请客的次数多。香港大户人家的小姐们,沾染上英国上层阶级传统的保守派习气,也有一种骄贵矜持的风格,与上海的交际花又自不同。对于追求薇龙的人们,梁太太挑剔得厉害,比皇室招驸马还要苛刻。便是那侥幸入选的七八个人,若是追求得太热烈了,梁太太却又奇货可居,轻易不容他们接近薇龙。一旦容许他接近了,梁太太便横截里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那人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末了总是弄假成真,坠入情网。这样的把戏,薇龙也看惯了,倒也毫不介意。
这一天,她催着睨儿快些给她梳头发,她要出去。梁太太特地拨自己身边的得意人儿来服侍薇龙;睨儿不消多时,早摸熟了薇龙的脾气。薇龙在香港举目无亲,渐渐的也就觉得睨儿为人虽然刻薄些,对自己却处处热心指寻,也就把睨儿当个心腹人。这时睨儿便道:「换了衣服再梳头罢,把袍子从头上套上去,又把头发弄乱了。」薇龙道:「拣件素净些的。我们唱诗班今天在教堂里练习,他们教会里的人,看了太鲜艳的衣料怕不喜欢。」睨儿依言寻出一件姜汁黄朵云绉的旗袍,因道:「我又不懂了。你又不信教,平白去参加那唱诗班做什麽?一天到晚的应酬还忙不过来,夜里补上时间念书念到天亮。你看你这两个礼拜忙着预备大考,脸上早瘦下一圈来了!何苦作践自己的身体!」薇龙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来,让睨儿给她分头路,答道:「你说我念书太辛苦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在外面应酬,无非是碍在姑妈面上,不得不随和些。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到这麽个机会,不能不念出些成绩来。」睨儿道:「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净受外国尼姑的气。那真犯不着!」薇龙道:「我何尝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活到哪里算到哪里罢。」睨儿道:「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我替你打算,还是趁这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式的人。」薇龙冷笑道:「姑妈这一帮朋友里,有什麽人?不是浮滑的舞男似的年轻人,就是三宫六嫔的老爷。再不然,就是英国兵。中尉以上的军官,也还不愿意同黄种人打交道呢!这就是香港!」睨儿噗嗤一笑道:「我明白了,怪不得你饶是排不过时间来还去参加唱诗班;听说那里面有好些大学生。」薇龙笑了一笑道:「你同我说着玩不要紧,可别认真告诉姑妈去!」
睨儿不答。薇龙忙推她道:「听见了没有?可别搬弄是非!」睨儿正在出神,被她推醒了,笑道:「你拿我当作什麽人?这点话也搁不住?」眼珠子一转,又悄悄笑道:「姑娘你得留神,你在这里挑人,我们少奶眼快手快,早给自己挑中了一个。」薇龙猛然抬起头来,把睨儿的手一磕磕飞了,问道:「她又看上了谁?」睨儿道:「就是你们唱诗班里那个姓卢的,拍网球很出些风头;是个大学生吧?对了,叫卢兆麟。」薇龙把脸涨得通红,咬着嘴唇不言语,半晌才道:「你怎麽知道她……」睨儿道:「哟!我怎麽不知道?要不然,你加入唱诗班,她早就说了话了。她不能让你在外面单独的交朋友;就连教堂里大家一齐唱唱歌也不行。那是这里的规矩。要见你的人,必得上门来拜访,人进了门,就好办了。这回她并不反对,我就透着奇怪。上两个礼拜她嚷嚷着说要开个园会,请请你唱诗班里的小朋友们,联络联络感情。后来那姓卢的上马尼拉去赛球了,这园会就搁了下来。姓卢的回来了,她又提起这话了。明天请客,里头的底细,你敢情还蒙在鼓里呢!」薇龙咬着牙道:「这个人,要是禁不起她这一撮哄就入了她的圈套,也就不是靠得住的人了。我早早瞧破了他,倒也好。」睨儿道:「姑娘傻了。天下老鸦一般的黑,男人就爱上这种当。况且你那位卢先生年纪又轻,还在念书呢,哪里见过大阵仗。他上了当,你也不能怪他。你同他若是有几分交情,趁早给他个信儿,让他明天别来。」薇龙淡淡的一笑道:「交情!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当下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