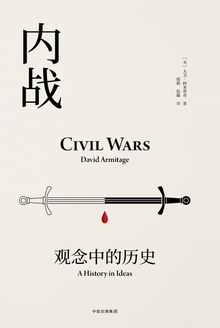第八章 (第1/6页)
肯·福莱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孩子死了。
简到达时,男孩已经死了近一个小时。她汗流浃背,满面灰尘,累得几乎摔倒。孩子的父亲站在洞穴口等她,麻木的神情中带着责备。从他松懈的体态和棕色眼睛中的平静不难猜出,已经完了。他一语不发。简走进洞穴看看孩子。她太过劳累,已经没有力气感到愤怒,强烈的失望感将她占据。让-皮埃尔不在身边,萨哈拉又处于悲痛之中,没有人能分担她的悲伤。
躺在杂货铺老板家屋顶的床上,她流下了眼泪。香塔尔就睡在身边一张小小的床垫上,睡梦中偶尔发出低声呢喃。她为死去的男孩哭泣,更为孩子的父亲难过。和她一样,那位父亲累死累活,拼尽全力也要拯救儿子。他承受的痛苦将是如何巨大。她在哭泣中入睡,泪水模糊了眼前的星辰。
她梦到穆罕默德睡在她的床上,在全村人的注视下与她欢爱;然后穆罕默德告诉她,让-皮埃尔有了外遇,与那个胖记者拉乌尔·克莱门特的妻子西蒙娜搞在一起。就在让-皮埃尔本应在科巴克坐诊之时,却是与情人在那里幽会。
由于前一天一路跑去小石屋,第二天简起床时,感到浑身酸痛。她一边进行着例行的琐事,一边想:自己算是幸运,让-皮埃尔在路上的一处石屋前停下来——大概是为了休息,这才使自己得以赶上。看到麦琪被拴在门前,看到让-皮埃尔和那个怪模怪样的乌兹别克男人坐在屋里,她这才松了一口气。进屋时,两个男人吓了一跳,好不滑稽。这还是简第一次见阿富汗男人会在女人进屋时起身相“迎”。
她带着医药箱走上山坡,打理洞中的诊所。她一面处理着普通的营养不良、疟疾、伤口感染以及肠道寄生虫病理,一面回想着昨日的紧急情形。在此之前,她从未听说过过敏性休克。毫无疑问,需要为他人注射青霉素的人通常也学过如何处理此类情形,然而她所受的培训实在过于匆忙,很多内容都被忽略了。事实上,医学上的细节问题几乎完全跳过,就因为让-皮埃尔是一位合格的医生,会在一旁为她指点。
那是一段怎样的苦恼时光:坐在教室里,有时身边坐着见习护士,有时确实独自一人,一边绞尽脑汁想要消化那些医学卫生原理与操作流程,一边想象着在阿富汗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生活。有些课程让她越听越觉得担忧。有人告诉她,她的第一项任务是为自己建一处土掩厕所。为什么?因为帮助落后国家人民改善健康状况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教他们停止把河流和小溪当作厕所,这样做可以为他们树立榜样。她的老师斯黛芬妮是一位戴着眼镜、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女人,经常是一身粗布衣服,脚蹬凉鞋。这位颇能生养的“大地母亲”还一直强调开药开得太过“慷慨”有多危险。多数的小病小伤不进行医疗处理也很快便会自动痊愈,可是那些“原始人”(以及那些“不算原始的”)总想弄些药片、药水来。简想起那个乌兹别克小个子一直在跟让-皮埃尔要水疱药膏。他一生中想必远路走了无数,见了医生才喊脚疼。过量开药的坏处在于不光是药品浪费,得了小病就吃药,久而久之,病人的身体便会产生耐药性;而等到病人身患重症,药物便起不到治愈的效果。斯黛芬妮建议简尝试与当地的传统医师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对立。简与接生婆拉比亚一直很默契,与毛拉阿卜杜拉则不然。
语言学习算是最简单的一部分了。在巴黎时,甚至是考虑去阿富汗之前,简便已经开始学习波斯语,好让身为翻译的自己更有用武之地。波斯语同达里语属于同一语种的不同方言。阿富汗地区使用的另外一个主要语种是普什图人使用的普什图语。达里语是塔吉克人使用的语言,而五狮谷地处塔吉克地区范围。少数游走四方的阿富汗人——例如游牧民族——通常通晓普什图和达里两种语言。如果再多会一门欧洲语言的话,则通常是英语或法语。小屋里的乌兹别克男人一直在跟让-皮埃尔讲法语。简还是第一次听人说带有乌兹别克口音的法语。听起来就像是苏联口音。
那一整天,她时常想起那个乌兹别克男人。一想到他,心中便是一阵烦乱。有时她明知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却又偏偏不记得是什么事时,那种感觉就是如此。这个人兴许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中午,她关闭诊所,喂过香塔尔,给她换了尿布,做了米饭和肉汁,与法拉共享午餐。这个小姑娘已经完全忠心于简,甘心做任何事讨她欢心,连晚上也不愿回家。简尽量对她平等相待,这样却使得小姑娘更加崇拜她。
正午炎热之时,简将香塔尔交给法拉,自己则下山来到自己的隐秘之地——山坡上悬石之下的一处阳光充足的隐秘崖台。她在那里进行产后运动练习,下定决心要恢复从前的好身材。她紧紧抓住盆底肌,脑子里一直想着乌兹别克男人,想到他在小石屋里起身站立,想到他那张东方人面孔现出惊愕的表情。她莫名地感到,悲剧即将发生。
然而发现真相的感觉并非是灵光一闪的顿悟,那种感觉更像是雪崩,刚开始规模很小,之后便是排山倒海。
没有阿富汗人会抱怨脚上起水疱,即使假装也不会,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这种东西:这就像格洛斯特郡的农夫说自己长了脚气——根本不可能。而且,无论多么惊讶,阿富汗人绝不会在女人进屋时起身站立。如果他不是阿富汗人,那又是何方神圣呢?他的口音也许一般人听不出,但简是个语言学家,熟练掌握俄语和法语,她听得出这个男人说的法语带着苏联口音。
也就是说,让-皮埃尔跑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石屋,去见一个伪装成乌兹别克人的苏联人。
是巧合?也算有可能,但想到自己进屋时丈夫的表情,她猛然想起了当时不甚留意的细节:他的神情里带着愧疚。
不,那不是偶然相遇,而是秘密约见。这可能甚至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让-皮埃尔经常要到边缘的村落坐诊——没错,他每次都坚持按时前往,那种谨慎未免显得过于夸张。处在一个没有日历,也不用日志的国家,这样的固执未免显得荒唐——除非他还另有打算,暗中策划着一系列秘密约见。
他为何要见苏联人?这一点也很明显,想到这些约见必然意味着背叛,热泪不由得涌入她的眼眶。他当然是为苏联人提供情报,把护送队的情况告诉他们。他对护送队的路线一清二楚,因为穆罕默德用的是他的地图。他知道大概的时间安排,因为他眼见队伍离开,从班达以及五狮谷其他村子出发。显然,他将这些情报交给苏联人;这就是苏联人去年多次成功突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才留下那么多悲伤的寡妇和孤儿,在五狮谷艰难度日。
我究竟怎么了?简突然自怨自艾起来,涌出的眼泪再次洗刷她的面庞。先是埃利斯,现在又是让-皮埃尔——为什么每次都碰上这种浑蛋?难道说我就喜欢这种行踪诡秘的男人?难道我享受打破对方心理防备的挑战?我真的那么疯狂吗?
她突然想到,让-皮埃尔曾经争辩苏联入侵阿富汗是有其正当理由,说着说着便改变了观点。当时她还以为是自己说服了他,证明他是错的。显然,这种改变是在演戏。当他决定来到阿富汗,决定为苏联人效力当间谍时,便开始用这套反苏言论为自己制造掩护。
难道他的爱也是在演戏?
光是这个问题就已经令她心碎不已。她将脸埋在双手中。这几乎无法想象。她爱上了这个男人,做了他的妻子,亲吻他那一副苦瓜脸的母亲,迁就他做爱的方式,与他一起熬过磨合期,拼尽全力维系他们的婚姻,在恐惧与痛苦中生下了他们的孩子——难道这一切就为了一个幻象,一副所谓“丈夫”的空壳,一个毫不在乎她的男人?这就如同连走带跑数英里只为询问如何拯救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到头来他还是失去了生命。不,比那还糟糕。她想象着,这想必就是男孩父亲的感受:背着他走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眼睁睁看他死去。
简突然感到前胸一阵饱胀的刺激感,一定是喂奶的时间到了。她穿上衣服,用袖子擦干脸上的泪水,然后向山上走去。悲伤渐渐淡去,她开始冷静地思考。结婚这几年来,她似乎总能隐约感到一丝失望,现在终于明白了。从某种方式来说,简一直都对让-皮埃尔的谎言有所察觉。因为有了这道屏障,两人之间一直都有距离。
回到山洞,香塔尔正在大声哭闹抱怨,法拉轻轻摇着她。简接过孩子抱在胸前,香塔尔吮吸着。起初她感到一阵不适,仿佛胃里的一阵痉挛;紧接着,她的乳房处感到一阵兴奋,甜美中带着欲望。
她想独自一人待着,于是告诉法拉回母亲的洞穴去睡午觉。
哺育香塔尔让简备感安慰,让-皮埃尔的背叛感觉也不再是五雷轰顶。她确信丈夫对自己并非虚情假意。那样做目的何在?又为何要带自己来到这里?自己对他的间谍行动毫无用处。一定是因为让-皮埃尔爱着她。
如果让-皮埃尔爱她,那么其他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他必须停止给苏联人卖命。简暂时还没想好如何跟让-皮埃尔摊牌——难不成要说“我全都知道了”?不行。但必要之时,她自然知道该如何表达。之后他则必须带着简和香塔尔返回欧洲——
回欧洲。一想到要回家,简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如果有人问她对阿富汗的感觉,简可能会说她的工作多么精彩、多么意义非凡,说她适应得很好,甚至十分享受这里的生活。然而如今,眼见就要重归文明社会,她的坚韧意志全然崩溃,她对自己承认:恶劣的环境、冬日的寒冷、陌生的人群、轰炸、源源不断送来男人与孩子残破的躯体已经让她濒临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她想,这里简直糟糕透顶。
香塔尔停止了吮吸,倒头便睡。简把孩子放下,给她换了尿布,然后把她放上床垫,孩子并没有醒。婴孩那种不受干扰的宁静实在是一种恩赐。她在睡梦中经历了各种危机——只要吃得饱,躺得舒服,什么样的噪声和活动都不会把她吵醒。然而,香塔尔对简的情绪变化感觉则十分敏锐。每次简感到忧虑时,即使周围没什么动静,香塔尔也同样会醒。
简盘腿坐在床垫上,望着熟睡的孩子,想着让-皮埃尔。她真希望丈夫现在就在身边,这样马上就能与他谈谈。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更加生气,更别说大发雷霆了——他可是将游击队的情报出卖给苏联人啊。是因为她终于明白所有男人都是谎话精?是因为她开始相信这场战争中唯一无辜的是交战双方的各位母亲、妻子和女儿?难道是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改变了她的个性,使得她面对背叛也不会怒从心生?还是仅仅因为她爱让-皮埃尔?她不知道。
总而言之,不能再与过去纠缠,得为将来做打算了。他们要回巴黎,回到一个有邮差、有书店、有自来水的地方。香塔尔可以穿上漂亮的小衣服,躺在婴儿车里,用上一次性的尿不湿。他们可以住在一所小公寓里,周围的生活丰富多彩,威胁生命的只有那些开出租的司机。简和让-皮埃尔可以重新开始,这一次,两人会努力真正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共同努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与合法手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不用阴谋,没有背叛。在阿富汗的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在第三世界发展组织,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找到工作。婚姻生活会像之前想象的那样,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不必担心危险。
法拉走进屋来。午睡时间已过。她礼貌地跟简打过招呼,看看香塔尔。看她睡得正香,便盘腿坐在地上等候吩咐。法拉是拉比亚大儿子伊斯梅尔·古尔的女儿。伊斯梅尔参加了护送队,目前不在家。
忽然,简忽然大惊失色。她喘着粗气,法拉诧异地看着她。简做了一个致歉的手势,法拉把头转开了。
她父亲也参加了护送队,简想。
让-皮埃尔把护送队的情报出卖给了苏联人。法拉的父亲一定会在伏击中牺牲——除非简能有所行动,以避免灾难发生。可她能做什么呢?她可以托一个脚力好的人跑去开伯尔山口与护送队会合,并把队伍领到其他路线上。穆罕默德可以安排。但这样一来,简就得告诉他护送队会遭受伏击——毫无疑问,穆罕默德肯定会杀了让-皮埃尔,很可能赤手空拳就结果他的性命。
简想,如果他们当中非要有人死去的话,那宁愿是伊斯梅尔,而非让-皮埃尔。
接着,想到谷里参加护送队的另外三十几个人,她突然意识到:难道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就要牺牲他们所有人的性命吗——小胡子卡米尔·汗、疤脸老头儿沙哈萨伊·古尔、有着一副好歌喉的尤瑟夫·古尔、小羊倌儿谢尔·卡多尔、没有门牙的阿卜杜尔·穆罕默德以及家里有着十四个孩子的阿里·加尼姆……难道要让这些人统统丧命吗?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她来到洞口向外张望。现在午睡时间已过,孩子们纷纷跑出来,在乱石与充满荆棘的灌木丛中继续着他们的游戏。其中有九岁的穆萨——穆罕默德唯一的儿子,如今只剩下一只手,家人对他更是宠爱有加,他拿着祖父送给他的新刀,显得得意扬扬。她看到法拉的妈妈正顶着一捆柴火艰难地朝山上走。毛拉的妻子正在清洗丈夫阿卜杜拉的衣服。简没有看到穆罕默德和他的妻子哈利玛。她知道穆罕默德在班达,因为早上刚刚见过。他一定是跟家人在洞里吃饭——多数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洞穴。穆罕默德现在应该在那里,而简不想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去找他,这会使周围人心生反感,而她必须谨慎行事。
我该怎么跟他说?简想。
她考虑单刀直入:既然我开口了,你就帮我个忙。如果换作任何一个爱慕她的西方男人,这招儿肯定管用;不过穆斯林男人对爱情的理解可没有那么浪漫,而穆罕默德对她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温存的渴求,远不至于令他为自己赴汤蹈火。再说,现在他的心意有没有变,简也不能确定。那怎么办?穆罕默德对她并无亏欠,她也从未给他们夫妇治过病。但穆萨则不然——简救过他的命。穆罕默德欠她这笔人情债。
帮我做件事,因为我救过你儿子。这样也许能行。
但穆罕默德一定会刨根问底。
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来,打水清扫自家的洞穴,照料牲畜,准备饭食。简知道,很快就可以见到穆罕默德。
怎么跟他说呢?
苏联人知道了护送队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