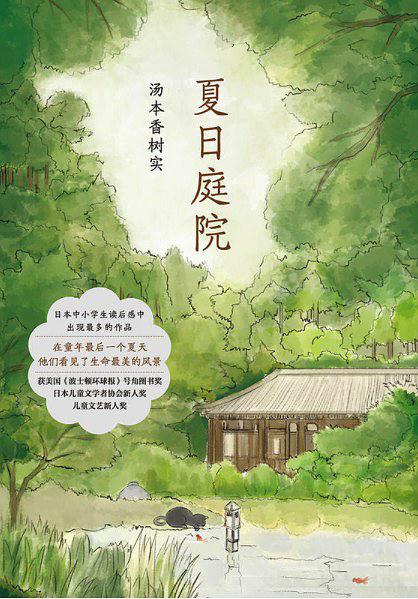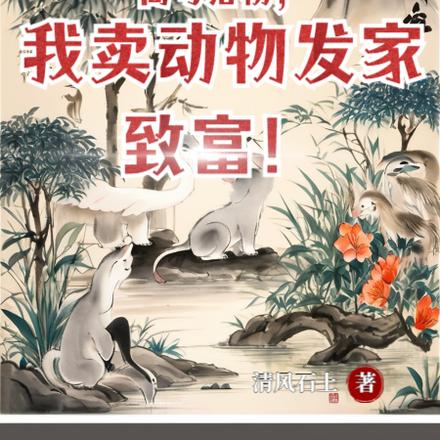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萨米哈:想到别人会说什么,费尔哈特就把我们的故事里最美好的部分作为隐私轻描淡写了。我们的婚礼虽然寒酸,却很美好。我们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蓝色公寓楼二层的白色苏丹婚纱店里,租了一件白色的婚纱。就像整个婚礼上我没犯任何错误一样,对于那些疲惫、丑陋和嫉妒的女人的骚扰,我也没有屈服。她们要么直接说,“啊呀,我的孩子,你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啊,可惜了!”要么因为没能这么含沙射影地表达,就用眼神表示,“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穷服务员,我们一点都不理解!”你们听我说:我不是谁的奴隶、小妾、俘虏……你们听我说:你们要明白什么是自由。费尔哈特喝着藏在桌下的拉克酒酩酊大醉,最后也是我让他清醒过来的。我仰起头,对那些嫉妒的女人和仰慕我的男人(其中也有来蹭柠檬水喝、蹭点心吃的无业游民),骄傲地扫了一眼。
两个月后,在邻居哈伊达尔和他的妻子泽丽哈一再坚持下,我开始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公寓楼里做用人。费尔哈特有时和哈伊达尔一起喝酒,他们夫妻俩还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我们好才希望我去打工的。作为一个丈夫,娶了抢来的女孩才两个月就让她去做用人,费尔哈特感到惭愧,因此一开始他反对我去帮佣。但是一天早上,我们和泽丽哈夫妇一起冒雨坐小公共去了加齐奥斯曼帕夏。费尔哈特也和我们一起,去了泽丽哈和亲戚们打工的吉万公寓楼看门人住的单元。比我们的单开间一夜屋还要小的这个地下单元,连一扇窗都没有。我们三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那小屋里喝了茶抽了烟,随后,泽丽哈把我带去了五单元的人家。爬楼梯时,我为将要进入一个陌生的人家而感到害羞,同时也因为要离开费尔哈特而感到害怕。私奔以来,我俩一直如胶似漆。我刚开始打工的那些日子里,费尔哈特每天早上和我一起过来,傍晚在看门人家里抽烟等我,下午四点我离开五单元下楼到憋闷的地下室,他或者把我送上小公共,或者把我托付给泽丽哈他们,确认我坐上小公共后,他才马上跑去幸福餐馆。但三周后,一开始是早上,快到冬季时,晚上我也开始独自来去了。
费尔哈特:为了不让你们对我产生误解,我要用一分钟时间插句话:我是一个知道负责任、勤劳和有尊严的男人,其实我是绝对不能容忍我的妻子出去打工的。但是萨米哈一再说自己在家无聊,想要出去工作。她没告诉你们,她为此哭过很多次。另外,我们与哈伊达尔和泽丽哈像家人一样,他们又和吉万公寓楼里的人像亲戚,甚至兄弟一般。因为萨米哈说,“我自己去,你听电大的课!”我才允许她独自去上班的。而这,在我学不进会计课,并且不能及时把作业邮寄到安卡拉的时候,让我感到更多的自责。眼下我又在担忧,自己记不住教授在数学课上写在黑板上的所有数字,从教授的大鼻子和耳朵里钻出来的白毛,在电视上都清晰可见。我之所以忍受所有这些磨难,是因为萨米哈比我还相信,如果有一天我拿到大学文凭,在一个国家机构里找到工作,那么一切都将会是另外一种情景。
萨米哈:泽丽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伤感易怒的女人,她住在五单元,是我的第一个“雇主”。“你俩一点也不像。”她说着用怀疑的眼神瞥了我和泽丽哈一眼。为了赢得她的信任,像我们事先说好的那样,我自称是泽丽哈父亲家的亲戚。纳兰夫人随即对我的善意表示了信任,可一开始她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能把四周的灰尘打扫干净。直到四年前,她还自己打扫卫生,那时他们也没有太多钱。四年前,她上初中的大儿子死于癌症,纳兰夫人便不屈不挠地向灰尘和细菌宣战了。
尽管刚看见我擦了那里的灰尘,她还会问:“你擦了冰箱下面和白灯里面吗?”我们害怕她的第二个儿子也因为灰尘得上癌症,因此在孩子快要放学回家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并更加拼命地擦灰,还不时跑去窗前,带着石砸魔鬼的愤怒,向街上抖落抹布上的尘土。“做得好,做得好萨米哈!”纳兰夫人鼓励我说。她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手指着我没看见的一处灰尘,“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灰尘和脏东西啊!”她绝望地说着并向我摇手指,于是我会感到自责,仿佛灰尘来自我的身上或是一夜屋街区。但我还是喜欢她的。
第二个月后,纳兰夫人信任我了,开始叫我一周去她家三次。她把我和肥皂、水桶、抹布一起留在家里,自己出去购物,或者去跟总在电话里聊天的朋友玩牌。有时,她借口忘了什么东西悄悄地回家,见我继续在勤勉地打扫卫生,就高兴地说:“干得好,愿真主保佑你!”有时,她拿起放在电视机上面、小狗摆件旁边的银镜框,镜框里镶着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她一边用抹布久久地擦拭着镜框,一边开始哭泣,我就放下手里的抹布过去安慰她。
有一天,纳兰夫人上街后不久,泽丽哈就来看我了。见我不停地干活,“你疯了吗?”她说道,打开电视坐到对面,但我还是继续干活。之后,只要她干活的那家夫人一上街(有时她家夫人和纳兰夫人一起出去),她就跑来找我。我干活时,她跟我说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翻冰箱找吃的,告诉我橄榄油做的菠菜味道不错,就是酸奶太酸了。(杂货店里买来的玻璃罐装的酸奶。)当泽丽哈开始翻纳兰夫人的衣柜,议论内裤、胸罩、手绢,还有那些我们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物件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跑去她身边,听她调侃,玩得很开心。纳兰夫人的一个抽屉的最里面,在丝绸头巾和围巾中间,有一个写着蚂蚁大小祷辞、念过经吹过气的护身符。在另外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我们在旧身份证、缴税单和照片当中,找到了一个很好闻的雕刻木盒,但不知道那是什么盒子。在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泽丽哈在纳兰夫人丈夫的药盒和咳嗽药水瓶子当中,发现了一种烟草颜色的奇怪液体。那个粉色的瓶子上贴着一张画,画上是个张大嘴巴的阿拉伯女人,我俩都最喜欢这个瓶子里的香味,但是因为害怕,不会把它抹手上。一个月后,当我独自一人翻东西时(我喜欢看纳兰夫人死去的儿子照片和旧作业本),我发现那个瓶子不见了。
两周后的一天,纳兰夫人把我叫到一边说,应她丈夫的要求(其实我没明白是谁的丈夫),要辞掉泽丽哈,尽管她确信我没错,可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继续干了。我没能完全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她开始哭起来,我也跟着哭了。
“我的孩子,不哭,我们为你找了一个好人家!”她带着乐观的口吻,犹如算命的吉卜赛女人说,“我看见了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希什利的一个有教养的富人家想找一个像我这样勤劳又诚实可信的女佣。纳兰夫人要让我去,我该二话不说立刻过去。
费尔哈特对我去新的人家表示反对,因为路程太远。早上我更早起床,天不亮就去赶开往加齐奥斯曼帕夏的第一班小公共。半小时后我坐上开往塔克西姆的公交车。在一个多小时的这段路程上,很多时候公交车里挤满了人,为了找个座位,人们在车门口争先恐后、你推我搡。我喜欢透过车窗看那些赶去上班的人、推着小车走向街区的小贩、停泊在金角湾的小船,特别是那些去上学的孩子。我仔细地去念挂在杂货店橱窗里的报纸上的大标题、墙上的布告、巨幅的广告牌。我若有所思地在脑子里重复着写在汽车和卡车车身上那些意味深长的句子,感觉城市在和自己交谈。我喜欢想费尔哈特的童年是在卡拉柯伊,也就是市中心度过的,回到家我让他讲那时的故事。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到塔克西姆换乘另外一辆公交车前,我从邮局门口的小贩那里买面包圈,要么在公交车上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吃,要么藏在我的塑料包里,等到了雇主家就着煮好的茶一起吃。有时家里的女主人说,“如果你还没吃早饭,就先吃吧。”我就从冰箱里拿出一点奶酪和咸橄榄。有时她什么也不说。中午我给夫人烤肉丸的时候,“萨米哈,给你自己也烤三个。”她说。她给自己拿五个,吃掉四个,我在厨房里吃掉剩在盘子里的一个,这样我们每人都吃了四个。
但是夫人(我不说她的名字就这么称呼她)不和我坐同一张餐桌,她吃饭时,我不能吃。“盐、胡椒在哪里;把这个拿走。”她要我待在可以听到她说话的地方,因此我就站在餐厅门口看着她吃饭,但她不跟我交谈。不时,她总问一些同样的问题,又总是忘记答案:“你是哪里人?”“贝伊谢希尔。”我回答道。“在哪里?我从来没去过。”于是我便说:“我是科尼亚人。”“啊,是的,有一天我也要去科尼亚,去拜谒莫拉维<small>18</small>。”她说。随后在希什利和尼相塔什的另外两家人家里,我说到科尼亚时,他们都问到了莫拉维,但都不愿意我做礼拜。泽丽哈告诫我,如果有人问“你做礼拜吗?”,要回答说不做。
夫人推荐我去的这些家里的人,也不愿意和我使用同一个厕所。在所有这些老房子里都有一个供用人使用的小厕所,有时我跟一只猫,有时和一只狗共用那个厕所,我的塑料手提包和大衣也放在那里。当家里只有我和猫咪时,猫咪总待在夫人怀里,还会去厨房偷食,有时我会打它,晚上回家后我就把这事告诉费尔哈特。
有段时间,夫人病了,如果我不能一直待在她身边,她就要再去找一个人,于是晚上我就在她那里,在希什利过夜了。我住在一个望向天井的小房间里,不见阳光却很干净,床上铺着的床单香气扑鼻,我喜欢那里。随后我就习惯在那里过夜了。去希什利一个来回需要花四五个小时,因此有些夜晚我就住在夫人家里,早上起来为她准备早餐,随后去别的人家干活。但其实,我想尽早回加齐,回到费尔哈特的身边,即便只有一天,我也想念我们的家和家里的东西。我喜欢下午早收工,喜欢在上公交车或者在塔克西姆换乘公交车之前,在城里转转,可是我又害怕遇到杜特泰佩的什么人,怕他们回去告诉苏莱曼。
留我一人在家时,他们有时会说,“萨米哈,干完活你就回家,别做礼拜、别看电视浪费时间。”有时我很卖力地干活,似乎想要擦去城市里所有的灰尘,但随后我会想到一件事,让我放慢干活的速度。我在先生放衬衫和背心的衣柜最下面的抽屉最里面,看见了一本外语杂志,杂志上有很多男人和女人的无耻图片,我为自己感到害臊,只为我看见了那些图片。夫人药柜的左侧角落里,有一个散发出杏仁味的奇怪盒子,盒子里的梳子下面有一张外国钞票。我喜欢看他们的家庭影集,塞在抽屉里的婚礼、学校放假和夏季度假时的旧照片,去发现他们年轻时的模样。
在所有的人家里,都有那么一个角落,堆放着丢弃、遗忘、落满灰尘的旧报纸、空瓶子、从未打开的盒子。他们说别去动,仿佛是一件宗教、神圣的东西。每个家里都有这样不让动、不让靠近的角落,没人时我会好奇地去看一看,但他们为了试探我而放在那里的新纸币、共和国金币、气味奇特的肥皂、长了虫子的盒子,我从不去碰。夫人的儿子,在积攒小的塑料玩具士兵,他在床上、地毯上把它们一排排地部署好,然后让它们激烈厮杀。我喜欢孩子忘乎所以地沉浸在游戏里,独自一人时,我也玩打仗游戏。很多家庭买报纸只是为了礼品券,他们让我每周剪一次。有些人家每月派我去一趟角落里的报亭拿礼物,类似搪瓷煮茶壶、带图片的烹饪书、花朵图案的枕套、挤柠檬汁的工具、会唱歌的圆珠笔。为了这些东西,他们让我去排半天的队。在电话上聊天度过一整天的夫人,有一个放毛料衣服的柜子,满是樟脑丸味道的柜子里有一套电动厨房用具,却像那些免费的礼品那样,从未拿出来使用过,哪怕是为了任何一个客人。因为那是欧洲货,总被仔细地收藏着。有时,看着我在柜底找到的信封里的收据、报上剪下的新闻和布告、女孩们的裙子和内衣、写在本子上的文字,就好像我找到一样寻觅已久的东西。有时,我觉得这些信件、文字都是为我而写的,照片上也仿佛有我的身影。抑或是,夫人的儿子偷了母亲的红色唇膏放进自己的抽屉,我感觉该我负责一般。对于这些向我公开隐私的人,我既感到一种依赖,又感到一种愤怒。
有时,我在正午想念费尔哈特、我们的家,以及从我们一起躺着的床上看见的发出磷光的地皮。开始做日工两年后,在越来越多留下过夜的日子里,我开始怨恨费尔哈特,因为不管怎样他都没能让我摆脱用人的生活。这期间我越来越深地融进了那些人家的生活,接触到他们残暴的男孩和娇惯的女孩,遇到觉得我漂亮就立刻跑来纠缠的杂货店伙计和看门人的孩子。每到来暖气时,睡在窄小的用人房间里,我总会大汗淋漓地醒来。
费尔哈特:从第一年开始,我就坐上了位于加齐奥斯曼帕夏的幸福餐馆的款台。我读电大在此起了作用,读电大也是萨米哈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但是晚上,当美妙的拉克酒和热汤味道飘散在餐馆、餐馆变得人声嘈杂时,老板的弟弟就坐上款台,亲自管理收银机,顺带自己的口袋……老板在阿克萨赖省还有一家餐馆(我们这里是分店),每个月老板都会向厨房里的厨师和洗碗工,还有我们服务员和传菜员重复一遍他的命令,那就是从厨房出来的每一样菜品,必须立刻在款台记录在案,否则不许端上客人的桌子。这些菜品如,炸土豆条、牧羊人沙拉、炸肉丸、盖浇鸡肉饭、单份拉克酒、小份啤酒、小豆汤、干扁豆、肉末大葱。
幸福餐馆,有四扇面向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窗户(每扇窗都拉着窗纱)。餐馆是一家拥有众多热情顾客(中午是一些不喝酒、吃家常菜的工匠,晚上是一些有节制喝拉克酒的男人)的成熟企业,因此要遵守老板的这个宪法规定也并非易事……我坐在款台时,也就是即便中午,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我都来不及记录服务员手上的蔬菜鸡块、橄榄油芹菜根、蚕豆泥、烤鲣鱼,都送去了几号桌。那种时候,要么像老板命令的那样,服务员在我面前排起队,等着让我记录;(着急的顾客喊道“菜凉了”,)要么推迟一分钟来执行老板的命令,服务员先把菜送给顾客,等我松快时回来提醒我,“费尔哈特大哥,十七桌一份辣椒塞肉末米饭,一份春卷,十六桌两份鸡胸肉。”这个办法不能解决排队问题,只是推迟了排队,也就是说,服务员开始把他们送给顾客的菜品,挨个其实是同时报出来让我记录,“六号桌一份沙拉,八号桌两份酸奶黄瓜粒。”有的服务员端着菜边走边报,记录的人无法听清他们所说的一切,因此有时会记错,有时像我做的那样随便编一个,有时就只好忽略不计了,就像我对待电视里听不懂的课程那样。服务员们知道,如果账单上的钱数低了,他们将得到更多的小费,因此他们从不抱怨被遗忘的那些菜品。而老板,不是因为损失了钱,而是不愿和顾客纠缠,有的顾客说,“我们没要两份,只要了一份酥炸贻贝。”因此他要求实施他定的规则。
晚餐时,我做服务员不看款台,因此我知道用心不良的服务员的所有诡计,中午我看款台时会注意这些。晚上,我也会不时采用一种最方便、精明的方法多挣小费,那就是给顾客上一份半的菜品,比如六个肉丸,账单上却只写一份,我将此讨好地告知可以信任的顾客,以此赚得更多小费。幸福餐馆里所有的小费都要放进同一个盒子里,为了名义上的公平分配(老板首先要拿一份),但没有一个服务员,会把拿到的所有小费全部放进那个盒子里,他们会在裤子和白色制服的一个口袋里,藏下一部分收来的小费。但这个问题不会导致任何指责和争吵,因为被逮到的人将被开除,也因为所有人都在那么做,因此没有一个服务员会去管别人的口袋。
晚上我照看入口处的几张桌子,另外一项工作就是为坐在款台上的老板当副手。这不是领班,而是一种代表老板的总督察职务。“你去看看,四号桌要的砂锅菜好了没有,他们一直在催。”老板说。尽管四号桌的服务员是居米什哈内人·哈迪,但我走去厨房,看见厨师在烤肉的烟雾中慢条斯理地烹饪后,我回到四号桌,用可爱的表情微笑着告诉他们砂锅菜马上就好。如果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就问要嫩一些,还是老一些,要放蒜,还是不要。没问题可问的话,我就问他们喜欢哪支球队,加入他们关于足球的聊天,我说我们的球队被算计了,裁判被收买了,周日那场球赛里没判给我们点球。
像往常一样,愚蠢的哈迪不时因为送错菜或上菜晚而让顾客造反,那时我就赶去调解,我不管下单的真正主人是谁,随手拿起厨房里的一大盘炸土豆条,或是在热油里吱吱作响的一大砂锅虾仁,作为餐馆的礼物,送到顾客面前。有时,我拿着一大份没有主人的混合烤肉,在没有点单的情况下,认真地用一种仪式(特意说“烤肉终于来了”),放到一群醉鬼的桌上,随后写进账单里。忘乎所以地聊着足球、政治和高物价的醉鬼们对此是不会有异议的。夜深后,遇到打架的,我去劝架;遇到异口同声唱歌让餐馆淹没在噪音里的,我去让他们安静下来;发生“开窗、关窗,开电视、关电视”的争吵时,我去化解矛盾;发现没把桌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倒掉的传菜员,我责备他们;看见服务员和洗碗工躲在厨房、走廊、门口和后仓库里抽烟,我用眼神打发他们回自己的岗位。
有时,周围律师和建筑师事务所的老板们带着女人请员工们吃午饭,或者戴头巾的母亲想让她调皮捣蛋的儿子们吃肉丸、喝阿伊兰,我们就让他们坐在门边为家庭保留的几张桌上。我们的老板在墙上挂着三张阿塔图尔克的画像,阿塔图尔克全都穿着便装,一张微笑着,两张带着犀利的眼神。老板的最大野心,就是女顾客光顾幸福餐馆,特别是在喝拉克酒的晚餐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够安心地和男人们坐在一起,满意地度过一个没有评头论足和争吵的夜晚,并再次光临。这在老板的眼里是一件大事,可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第二个愿望,在餐馆有争议的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但凡来了一个女顾客,第二天老板一定会恼怒地模仿餐馆里其他男人如何像“看火车的公牛”那样看她的丑态。他要求我们服务员能在这样一个女顾客再次光临时不要慌乱地一拥而上;要求我们见怪不怪,礼貌地去警告其他桌上那些脏话连篇、大声说话的男人;要求我们让女顾客远离公牛们令人厌恶的目光。最难实施的就是老板的最后这道命令。
夜深后,遇到最后一拨醉醺醺的顾客怎么也不肯离去时,老板就对我说“你快走吧,你家住得远”。回家的路上,我带着自责和思念想到萨米哈,认定让她去做女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早上我起床时,她早就出门了,我为自己同意她去打工而感到后悔和痛苦,我咒骂自己的贫穷。下午,合住一个单身宿舍的三个洗碗工和传菜员说笑着择四季豆、削土豆皮时,我坐在角落里的桌子上,打开面前的电视机,全神贯注地努力领会土耳其广播电视协会TRT播放的远程会计课程。有时,课是听懂了,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做随信寄来的作业。我站起身,梦游般地走出幸福餐馆,绝望并愤怒地走在塔什勒塔尔拉的街上,幻想着就像电影里那样,用武力劫持一辆出租车,不管她干活的人家在希什利的什么地方,去找到萨米哈,和她私奔到城市另外一个边远街区里的我们的新家。这个新家,在我的脑海里,总是和我幻想中想盖的房子混在一起。我幻想着用攒下的钱,在我们从后窗看见的那块发出磷光的地皮上,盖一个四扇门、十二个房间的房子。或者,下午五点钟,穿上漂亮的服务员制服,开始上班前,从洗碗工到领班,幸福餐馆的所有员工,坐在最后一排长桌上,围着摆放在桌子中央的大锅,喝着加了肉丁和土豆丁的蔬菜汤,吃着新鲜面包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明明可以在市中心自己创业,却偏偏要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耗费生命,我悔恨地感到这种耗费的痛苦。
萨米哈回家的那些夜晚,老板看见我迫不及待地想尽早下班,“新郎官先生,脱下你的制服,回家去吧。”他说。我感激他的善心。萨米哈来过餐馆几次,其他的服务员、传菜员、洗碗工,所有人都见证了她的美貌,他们笑着叫我新郎官时,我知道他们在嫉妒我的好运。夜晚等待总也不来的加齐公交车时(公交车开始去我们的街区了),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这份好运而悲哀,我变得更加迫不及待,想到我做了一件错事,不禁陷入恐慌。
开往加齐街区的公交车走得那么慢,靠站的时候又是那么慢条斯理,我坐在座位上不停地晃腿。到了最后几站,当一个赶车的人在黑暗中叫到“司机,司机,等一等”时,司机便点上一支烟等着,我坐不住站了起来。从最后一站到家的那个大坡,我忘却疲惫跑着往上爬。黑夜的宁静、远处一夜屋灰暗的灯光、几个烟囱里冒出的难闻的褐煤烟雾,所有的一切,全都变成了提醒我萨米哈在家等我的标记。今天是周三,她一定在家里。也许和很多时候一样,她已经累得睡着了。我便去想她睡着时的美丽模样。也许,像她有时做的那样,她为我煮好了菩提茶,开着电视,在等我。她那聪慧、友善的模样闪现在我眼前,我开始奔跑起来。好像我一奔跑,内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萨米哈一定在家等我的信念。
如果她不在家,为了平复恼怒和痛苦,我就马上喝拉克酒,责备自己。第二天晚上,当我得以更早离开餐馆踏上回家的路途时,我会再次经历同样的迫不及待。
我见到她时,“对不起,”萨米哈说,“昨天夫人有客人……她一再坚持让我在她家里过夜,她给了我这个!”我把她递来的纸币放到一边,“你不要再去打工了,你不要再走出这个家门。”我激动地说,“咱俩都永远不走出这个家门。”
头几个月里萨米哈说,“那咱们吃什么?”后来她就笑着说,“好,我不去打工了。”当然早上她还是继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