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又上路了!嗨,熟悉的车站,摇摇晃晃的巴士,悲伤的旅人,哈罗!一切就是如此发生,你已经习于某些固定的生活模式,当日常琐事离你而去,你变得沉溺其中,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已经陷入这些习惯中不可自拔;你察觉日子再也与过去不同了,悲伤紧箍着你不放。我原本以为,搭上这辆玛吉鲁斯公司老旧的巴士,远离妙医师秘密王国管辖的卡提克小镇,朝文明社会而去时,自己不会有半分感伤。毕竟,我已端坐在巴士上,尽管这辆车引擎噗噗作响,爬山路时上气不接下气,活像抽搐呻吟个没完的怪老头。但是,在那个如故事书中美景的土地最深处,在嘉娜倒卧的那个房间,那只我没能摆平的蚊子还在,而嘉娜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等待夜色降临。我重温一遍资料,再盘算了一会儿,以便可以早点把事情处理完毕,凯旋而归,迎来我的新人生。
约莫夜半时分,另一辆巴士上,我在半梦半醒间睁开眼睛,把脑袋从震动的窗户上移开,心中愉悦地忖度,噢,天使,或许,我将在这里首次与你面对面相会。要走多远、要等多久,才能把纯净的灵魂与绝无仅有的神奇一刻圆满结合,这是激励我一直走下去的动力。我知道,恐怕没办法那么快从巴士窗口望见你。漆黑的平原、阴森的峡谷、漾着水银般色泽的河流、废弃的加油站,还有文字掉落不全的香烟、古龙水广告看板,一个个呼啸而过,而在我的脑海中,只充满邪恶的阴谋、自私自利的意图、死亡,还有,那本书。我对荧幕上放射的红光视而不见,虽然它或许能刺激我的想像力;至于片中日日大开杀戒、回家便呼呼大睡的屠夫,对他发出的可怕鼾声,我同样充耳不闻。
天快亮时,我在一座名唤阿拉卡利的山城下车。时序已跳过秋季,更遑论夏末,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坐下,等待公家机关开门办公。负责清洗玻璃杯、泡茶的那个男孩,发线几乎生在眉毛位置,似乎没有额头可言。他问我是不是来听教主授道。为了打发时间,我告诉他“是”。他特地泡了一杯浓茶给我,与我分享他的喜悦。他告诉我教主的神迹,说除了治疗病患、帮助不孕妇女怀胎,其实教主真正的特异才能,是只要注视着叉子它便会弯曲,还有只要轻轻碰一下瓶盖,百事可乐就自动开瓶。
当我离开咖啡馆,冬天已经远离,秋季再度被略过,现在已经是炎热、蚊蝇满天飞的夏日时节。我就像个顿时摆平一切问题的成熟稳重高人,迳直朝邮局走去,心中有—抹隐约的兴奋。我小心翼翼地环视室内,满脸睡意的男女职员,有的在座位上看报纸,有的抽着烟,有的正倾身在柜台上喝茶。本来以为可以从那位一脸慈爱大姐相的女职员口中问出一点东西,没想到她居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婆娘,一迭连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你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不在这里等?不过先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可以晚点再来吗?我满头大汗,逼不得已只好告诉她,我来自伊斯坦堡,是穆罕默德军中的同袍,和邮政总局的董事会关系还不错;她这才告诉我,穆罕默德·布尔登刚离开送信去了。刚刚离开一会儿的穆罕默德,现在已经隐身邻近的巷弄街道之中,得费一番工夫才能找到,我绝望地转了大半天,被那些街名搞糊涂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见人就问,嗨,你好,邮差穆罕默德来过了吗?——我在附近的窄巷中不断迷路。一只花斑猫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舔着自个儿的毛。阳台上有个颇具姿色的年轻妇女正在晾床单、被褥和枕头,几个市府工人将梯子靠着电线杆爬了上来,和她眉来眼去。我看见一个生着一对漆黑眼珠的男孩,他一眼就看出我是外地人。“有何贵干?”他趾高气扬地问。假如嘉娜跟在身边,或许她马上就会与这个自作聪明的小鬼交上朋友,机灵地嘲弄他一番,而我将明白自己之所以对她彻头彻尾倾心至此,不是由于她的美貌,不在于她魅力无法挡,不单是她如此神秘,而是因为,她很快就能与那小鬼攀谈起来。
邮局正对着凯末尔雕像,对街则有一家叫作“翡翠”的咖啡屋。我在人行道西洋栗树树下的桌旁坐下,过了半晌,发现自己居然看起了《阿拉卡利邮报》:当地药房从伊斯坦堡购入一种治疗便秘的新药,以“屎脱拉肚”为名发售;被伯鲁竞技足球俱乐部炒鱿鱼的教练刚来到镇上,将执教下一季大有可为的阿拉卡利砖厂少年队。所以,看样子镇上有座砖厂,正这么想着时,我瞧见穆罕默德·布尔登肩上垂着两大袋邮包,气喘吁吁地走进镇公所,真是让我失望透顶。这个外表粗拙、疲惫得像狗一样狼狈的穆罕默德,一点也不像那位令嘉娜为之神迷疯狂的穆罕默德。
我在这里的任务已了,想到名单上还有许多年轻的穆罕默德等我造访,我还是不要打扰这个清幽平静的小镇,走为上策。但是,心魔却驱使我,在原地等着那位穆罕默德跨出镇公所大门。
就像其他邮差一样,他踩着小碎步,快速穿过马路,朝阴暗的人行道走去。我喊他的名字,叫住了他,他迷惑地看着我。我对他又抱又亲,责怪他连军中最要好的伙伴都认不出来。他内疚地和我一块儿坐下,我残忍地继续耍弄他,要他至少“想出人家的姓”,他开始乱猜一通。过了一会儿,我猛然打断他,告诉他一个随便捏造的假名。我告诉他,自己认识一些邮政总局的要人。他看来像个老实的小伙子,甚至对升迁没有兴趣。大热天扛着沉重的邮包,已经把他累坏了,汗水正如雨下。侍者端来清凉的汽水,他感激地望着,很快打开瓶盖。他心里很想尽速逃离这个可疑的军中弟兄,不是由于把对方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觉得羞赧想开溜,而或许是因为睡眠不足,但是,我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直冲脑门。
“我听说你读了一本书!”我说着,严肃地啜了一口茶:“我听说,你根本不在意别人看见你在读那本书。”
他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他对我的话题了然于胸。
“你从哪里拿到那本书?”
但他很快便恢复镇定。当时他在伊斯坦堡的医院陪伴住院的亲戚,那本书是在路边一处书报摊发现的。他被书名混淆,以为那是一本关于养生的书,因此买下它,后来舍不得扔掉,送给了那位亲戚。
我们停顿了一会儿。一只麻雀停在桌旁的空椅子上,然后再跳到另一张空椅。
我端详着这位邮差先生,他的名字以小写字体工整地写在口袋上。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许此我稍大一些。他也碰上那本令我人生方寸大乱、导致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的书,他同样感受到那本书带来的冲击,他和我一样慌乱震惊——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慌乱,或者说,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了解他的心情。我们的共同点,让我们同为受害者,或同为赢家,想到这点就让我很不爽。
我发现,他并没有低估这个话题的严重性。因为暍完汽水之后,他便俐落地把瓶盖一扔。我觉得,在他心中,那本书有不寻常的地位。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有一双极漂亮的手,手指修长优雅;他的皮肤甚至称得上细皮嫩肉;他有一张敏锐的脸孔,杏眼透出易怒、容易陷入忧郁的个性。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和我一样,亦受了那本书的蛊惑吗?他的世界也全变了样吗?午夜梦回,当那本书让他觉得自己在世上竟可悲、孤单至此时,他是否也一样陷入哀伤?
“不管怎样,”我说:“老朋友,今天很高兴。不过,我得赶巴士去了。”
为了让这个人与我袒裎相见,我仿佛对他揭露自身的创伤般,把自己痛苦的心掏出来给他看。天使啊,原谅我的不得体与粗鄙,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些不在计划中的行为,我竟然都做到了。倒不是我讨厌那些表现真心诚意的老套交际手法,这类相聚最后不是喝得烂醉,就是哭成一团,伤心欲绝,这种情感不能仅以哥儿们间的感情解释带过——事实上,我还挺喜欢和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到破旧的小酒馆喝两杯呢。我现在不想这么做,因为除了嘉娜,我不愿想及其他。我希望快快独处,让自己满脑子梦想着,有一天能与嘉娜同享欢乐的婚姻生活。我才刚站起身,我的军中伙伴便说:“这个时间,没有巴士到附近的任何城镇。”
接招吧!他不是笨蛋!他抓到我的小辫子,得意洋洋地以那双漂亮的手反复轻搓着汽水瓶。
我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掏出枪住他的细皮嫩肉上打几个窟窿,还是变成他的好哥儿们、知心密友和命运共同体。或许我该折衷一下,比如说一枪击中他的肩膀,又感到懊悔,急忙将他送到医院;之后当夜幕低垂,他的肩头缠着绷带,我们把他邮包里的所有信件逐一拆开阅读,疯狂作乐一番。
“无所谓。”我把钱放在桌上付了帐,洋洋得意地说,然后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从哪部影片学来的,不过学得不赖。
我像个认真、有干劲的人一样健步如飞,他或许正望着我离去。我绕过凯末尔雕像,步上窄小的阴暗人行道,朝巴士站而去。这个地方称之为巴士站未免溢美,因为充其量它只是个让巴士挡雨挡雪的草棚罢了,根本不会有任何巴士。我倒楣到得在穷乡僻壤的阿拉卡利小镇过夜——我的邮差朋友,可是称这个地方为“城市”。一个认真尽职、以自己工作为荣的男人好心地告诉我,中午以前没有巴士。这个人真是倒楣透顶,终其一生都得待在一间小斗室卖票。当然,我没有多此一举告诉他,他那颗秃头和他背后固特异轮胎广告中的美女大腿,一样是橙色。
我为什么这么火大呢?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脾气这么坏?天使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何方,告诉我吧,求求你,指点迷津吧!请你照护我,至少,警告我不要在盛怒下胡乱开枪;让我竭力把事情处理妥当,让我像个爱家顾家、一心一意保护家眷的男人一样,摆平世上所有病痛与不幸;让我和发高烧的嘉娜重新聚首吧。
但我心底的怒火却茫无头绪地四处乱窜。难道,每个带枪的二十三岁男孩,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我浏览着笔记,很容易就找到那条街,以及打算前往的商家:救世杂货铺。手织的桌布、手套、婴儿鞋、蕾丝、念珠全部稳妥地放在小窗台上,极有耐性地暗藏诗意,吹皱妙医师手下手表密探们心中的一池春水。我走进店铺,望见老板正在看《阿拉卡利邮报》。我不确定是否该跟他打照面,所以又转过身。阿拉卡利镇上的人,难道都这么自信吗?还是只有我这么想?
我坐在咖啡馆里,心中有些微挫败感。灌下一瓶本地生产的汽水之后,我脑中盘算着该怎么做。我去买了一副墨镜,其实之前经过药房的人行道时,便已经在窗口看上它了。勤奋的老板剪下报上的泻药报导,贴在窗子上。
当我戴上墨镜,走进救世杂货铺变得轻而易举,顿时变身为自信十足的当地居民。我沉着声,要求看手套,母亲总是这么做的。她从来不会说“我想为自己找一双手套”,或是“我需要替当兵的儿子找一双中等尺码的羊毛手套”,而会直截了当地请求:“我想看手套!”为了让她满意,店里总是引起一阵骚动。
但对这位老板兼伙计来说,我的指令一定犹如天籁。他小心翼翼地瞥了我一眼,让人联想到爱挑剔的家庭主妇,又像个一心想升官,把军阶徽章配挂得整整齐齐的小兵。他把所有货品从抽屉、手织包包及展示窗中,全部拿出来给我看。他看来约六十开外,脸上蓄着短须,嗓音透着坚定,表现出对手套的迷恋。他让我看手织的女用羊毛小手套,每根手指都花花绿绿地织上三种不同颜色的毛线;接着,他把牧羊人最爱的粗毛手套由内向外翻开,展示缝在内里的马拉什山羊毛皮,说可以强化手掌;这些毛线都没有使用人工染料,全都是他亲自挑选,并由乡村农妇依他设计的式样编织而成。他的指尖磨出一层皱皮,因为指尖部位是毛手套最容易磨损的地方。如果我想在手腕处加上一朵花,应该买这一双,它以最纯质的茶色染成,边缘镶以蕾丝;或者,我有什么特别偏爱的款式。他问我要不要拿下墨镜,好好瞧一瞧这双由色瓦斯出产的康嘎尔狗皮所制成的高级奇品。
我看了看,又戴上墨镜。
“惊慌孤儿,”我说,那是他在通报消息给妙医师的信件中使用的假名:“妙医师派我来,他对你不太满意。”
“怎么会呢?”他镇定地问,仿佛我只是把话题转到手套颜色那般简单。
“邮差穆罕默德是无害的公民,你为什么想加害这样一个人,举发他?”
“不,他可不是那么无害。”他说,带着介绍手套的口吻解释:那家伙一直在读“那本书”,而且挺引人注意。很显然,他脑袋里装的阴险邪恶思想,均跟那本书脱不了关系,满脑子也都充满那本书意图散播的毒素。有一次,他在某位寡妇家被逮,因为他以送信为借口,没敲门就擅自闯入。另外一次,他和一个学生脸颊紧贴,膝头紧靠在一块儿,在咖啡馆看儿童漫画;其中一本画册,内容以评鉴圣徒与先知的标准评价土匪无赖和窃贼。“光这样还不够举发他吗?”他问。
我不太确定,没有作声。
“如果,今天在本镇……”没错,他用了“本镇”这个字眼说:“禁欲的美德被视为耻辱,手指涂抹指甲花的女性被人看不起,那么,这都是拜邮差、巴士,还有咖啡馆里的电视所引进的美国货之赐。你搭哪班车过来?”
我照实答了。
“妙医师,”他说道:“无庸置疑是个伟大的人物。依他的指示行事,令我心境平和,我感谢上苍。不过年轻人,你回去告诉他,别再派人盯我了。”他收拾好手套说:“顺便再告诉他,我在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的公厕亲眼见到那个邮差在自慰。”
“而且,是用他那双纤纤玉手呢。”说完我便离开。
原以为自己到了屋外会舒服些,但是当踏在被艳阳晒得如烤盘的石子路上,我惊怖地想起,自己还得在这个小镇消磨两个半小时。
我静静等着,觉得快晕倒了,全身虚脱。最惨的是我没有睡好,胃里满是一杯杯灌下的茶水、菩提茶和可乐,脑中爬满从《阿拉卡利邮报》读来的一则则当地短闻,视线所及尽是镇公所的红瓦屋顶,而农夫银行那闪闪发亮的红紫色招牌像海市蜃楼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我耳中充塞着鸟儿的鸣唱、发电机的嗡嗡声和旁人的咳嗽声。当巴士总算精神抖擞地转进站,我急切地霸住门口,但被一把推开。后面的人把我拉回来,以免我挡住神圣教主的去路——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摸到我身上的华瑟枪。教主飘着仙气晃过我身旁,淡粉色的脸庞闪耀着智慧的神采,让他浑身散发高尚的光辉,仿佛对我们这些堕落的生灵满怀痛惜之心;不过,他对自己引发的骚动,似乎相当得意。何必要取枪呢?我自言自语,感觉腰间的枪正抵着腹部。我上了车,没有骂半句话。
坐在三十八号座位上,我发现巴士并没有离站,而且觉得嘉娜和她身边的世界都已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禁不住去瞧外面欢迎教主的人潮,看见目前正轮到咖啡馆那个小厮亲吻教主的手。当巴士开动时,我注意到他得体地吻罢教主的手,并小心翼翼抬起那双手,触碰自己的前额。此时,我注意到那位悲痛商人也在其中。他像个下定决心行将暗杀政坛领袖的刺客,穿过丛丛人群。但是,当巴士驶离,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打算靠近教主,他的目标是我。
小镇被巴士抛在后方,忘了吧,我告诉自己。阳光像个灵巧的探员,一直紧抓着我的座位不放。无论上路几回,即使身在树下的阴影中,它也下放过我。阳光无情地烤着我的颈背与臂膀,活像在烤面包。但我一直告诉自己,算了,算了,没关系。这辆有气无力的巴士吐着气,在这片没有房舍、没有人烟、片林不生、不见半块岩石的荒凉黄土地上一路吁吁前行,我惺忪的双眼却被光线照得一片昏花。我知道,不要理会它,随它去吧,这时候,是其他的事让我的头脑深处得以保持异常清醒。悲痛商人提报了我邮差朋友穆罕默德的大名,我在那个小镇盘桓五个小时,这段时间某些事已经有谱了——我该如何汇整资讯?像我这样业余的侦探,往后行经各城镇时,应该观察哪些多彩、和谐的景象与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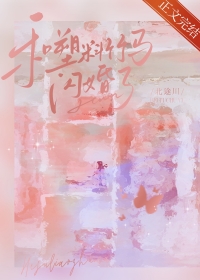


![大佬偏偏要宠我[穿书]](https://jmvip3.com/images/15094/77e7f3bca28fd27db1afbaa0ebd90e24.jpg)

